安德瑪衝鋒衣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袁亞棋寫的 微光長旅:從南非出發 和MerlinSheldrake的 真菌微宇宙: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動世界、推展生命,連結地球萬物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經典雜誌出版社 和果力文化所出版 。
輔仁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包哲所指導 盧宣合的 第三帝國男同性戀迫害。原因及影響。 (2003),提出安德瑪衝鋒衣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優生學、種族主義、遺傳健康照護、種族血統維護、绝、育、同性戀迫害、刑法第175條、集中營。
微光長旅:從南非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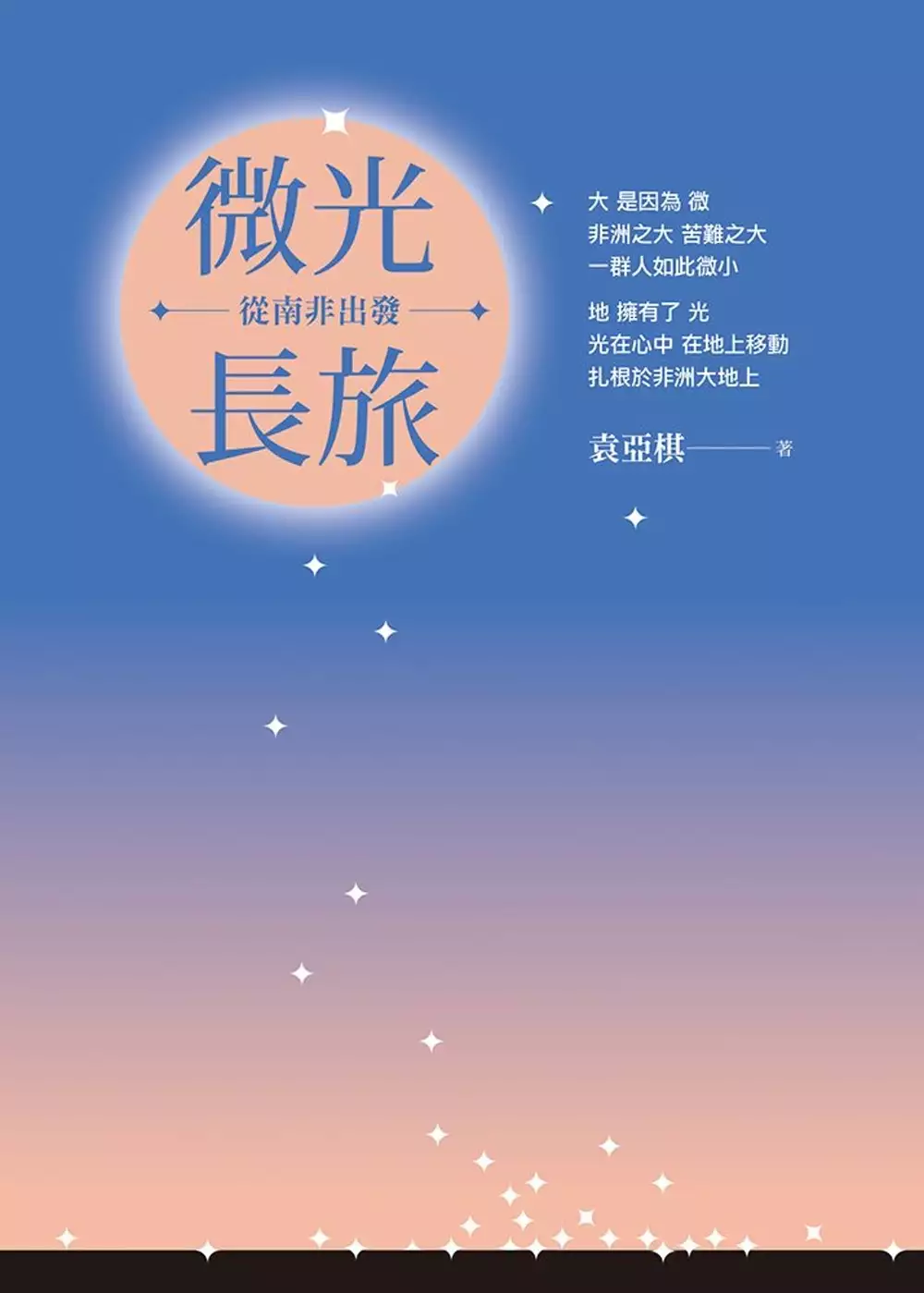
為了解決安德瑪衝鋒衣 的問題,作者袁亞棋 這樣論述:
光是劃破黑寂大地的第一道自然 並且永遠都是 大是因為微 非洲之大 苦難之大 一群人如此微小 地擁有了光 光在心中 在地上移動 扎根於非洲大地上 來自臺灣的南非媳婦,認識了黑、白兩道,衝破了善、惡界線, 她以真心為墨、以牽掛為紙,手執衝鋒陷陣的筆,記錄下非洲的心面貌。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多數的人對於非洲的理解,依然處於單一故事中的貧窮、饑荒、疾病等印象,雖然這的確是非洲現存的真實元素之一,但以慈善工作來說,如果也只是用如此既定的元素去理解非洲,其實是非常不足的。 這像是外界拿了一個貼滿標籤的沈重包袱硬要讓非洲人背上,背著背著習慣了
,人們漸漸也以包袱上的詮釋來理解自己,一不小心還發現,只要背好包袱,獲得外來同情的機會就更多、援助也更多。他們如同被注入了某種失憶針,不自覺地慢慢掉落自身本有堅韌天賦的記憶。當人習慣於遺忘自己還擁有什麼時,這將是比標籤上的問題還更嚴重的問題。 一九九四年,臺灣募集了兩大貨櫃的愛心衣物運到南非,為了協助慈濟發放,移居南非的潘明水開始接觸慈濟。進而深入部落,協助與帶動受到家暴的婦女、奄奄一息的愛滋病患走出心靈牢獄,不僅獲得重生,其中更有人轉身成為到處助人的志工。 廣袤的南部非洲,因為氣候極端,基礎設施又很薄弱,使得資源得不到有效的開發,人民普遍窮苦;尤其女人地位低下,更是苦中之苦。然而
走出家門對他們來說,如同久處暗暝終於看到一道光一樣,原來幫助人是這麼簡單,得到的回饋卻是這麼的快樂。 在潘明水的引導下,自二〇一二年組織一支「德本國際志工團隊」,到史瓦帝尼跨國傳愛開始,這幾年來,相繼進入莫三比克、波札那、納米比亞、馬拉威,最近又跨入尚比亞。在每個國家找出有心有潛力的種子,用愛灌溉和陪伴,期待能一生無量,在非洲堅硬的土石上栽培出希望之花。 他們如同螢火蟲的點點微光,從南非德本漸漸向外擴散,力量雖小,但期盼點點微光能化做一股股暖流,溫暖與自己同樣受苦的非洲苦難暗角。 而從臺灣嫁到南非的作者袁亞棋,因緣際會與南非這些本土志工併肩地致力於當地慈善工作,一起打拚,一起
積累生命的光芒。親見人間最晶瑩真實、最用力綻放的點點微光,她誓願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將它們守護下來,化成字字誠懇的篇章。期盼能夠牽動愈來愈多人一起來關心、投入,讓非洲愈來愈好,也讓世界愈來愈多愛。 二〇二一年七月,南非發生暴動,在這之前是新冠疫情,至今依然在全球肆虐,然而誠如置身其中的作者云:世界或許總有向下沉淪的拉力向我們挑戰,然而真正的微光,又怎會懼怕在黑夜中,持續釋放光華呢!?就像奇瑪曼達也是這樣說,「當我們了解世上沒有任何地方只有單一個故事時,我們就會重拾心中的樂園。」
第三帝國男同性戀迫害。原因及影響。
為了解決安德瑪衝鋒衣 的問題,作者盧宣合 這樣論述:
第三帝國男同性戀迫害。原因及影響。 1.0 納粹掌權前男同性戀者的處境 德國最早規定嚴重偏差性行為罰責的法律為西元1507年Bambergische Halsgerichtsordnung第141條,條文規定凡是人與牲畜、男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進行不正常性行為得判死刑。西元1532年的加洛林納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第116條中亦可找到完全相同的條文採用。18世紀末時的同性戀行為罰責獲得了較輕的罰責-從死刑減為監禁。 西元1855年時在巴伐利亞甚至將同性戀除罪。
西元1827年的普魯士曾提出同性戀的除罪草案,但是直到西元1851年時此草案終究未通過,在刑法第143條的修法時更加重同性戀行為的罪行。 基本上同性戀的法律刑責的全面修改則在西元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的刑法第175條,但是當時的法條對什麼是同性戀行為的定義並不明確,反倒要經由法院的判決來界定。西元1871年5月15日最後版本的刑法第175條是如此規定的:兩個同性男子或人與動物從事違反自然的性行為處以監禁及剝奪公民權。 2.0 優生學的起源和發展 2.1 概論 2.2 達爾文的演化論
西元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出版了演化論(Origin of Species),他在書中闡釋了生命如何經由「變異」和「挑選」而繁衍下去,這樣的觀點在當時帶來了生物學上的革命,其理論的重點在於物種是經由一段長時間的過程慢慢轉變而來,同時物種的存活更視其在環境中的適應能力而定。達爾文早期的理論主要著重於物種的演化,但是在後期的著作中,特別是論人類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書便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他在書中說:種族的體質會產生偏差,像是對氣候的適應、對不同疾病的抵抗程度均是,情緒上的反應亦不同,部份的種族在智能上也會有差異。
達爾文雖然不像其他著名的種族主義者般立場鮮明,可是依舊帶有種族主義的思想。除此之外達爾文亦贊成節制孱弱的人及病人的繁衍,在這點上便是優生學上的態度了。 第一個將達爾文的演化論運用在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關係上的德國人是黑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他說:伴隨文明發展而來的醫藥、衛生進步為人類帶來了危險,因為這些會使自然的淘汰機制(天擇和生存競爭)失去效力,並讓俱有遺傳疾病的人有機會存活,如此一來便會敗壞整個民族。黑克爾強調要回復自然法則的效力。 2.3 種族主義的由來和發展 種族主義的概念早在
「種族」一詞被運用前即存在於西班牙。西元1391年猶太人遭強迫受洗為天主教徒,儘管如此,皈依為天主教徒的猶太人在法律上和社會上的地位依舊得不到平等的對待,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西班牙充斥「血統純淨」的迷思。這種對「血統純淨」的意識形態而後也在西班牙的殖民地開展,提供現代種族主義的遵行原則。 種族的觀念可能始自於阿拉伯文中的raz,此字意謂頭部、領導者、王室、貴族家族,13世紀後這個字便可從羅馬語系的各語言中發現。 法國醫生貝寧(Francois Bernier,1620-1688)最早把「種」這個字運用到人類身上;而瑞典醫生林內(Carl von Linne
;,1707-1778)將原本運用在植物、動物上的分類法也使用在人類身上,他把人類分為白、紅、黃、黑四類,並賦予道德價值上的區分,以白人為最優秀,黑人為最低下。 英國主教、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也將人類分為五類,而以白人為最優秀。自此之後,種族不再只是單純地、描述性地為形態的區別而已,同時摻雜道德上以及智能上的價值判斷。 戈比諾(Josef Arthur Gobineau,1816-1882)在西元1853/1855年出版他的論人類之不平等,這本書成為後來種族主義思想的重要基石。戈比諾也談到作為核心種族的人種是最高等的種族
,其代表-亞利安種族-分布在英國及北德等地區,是「無可爭議地最為高貴」。至於「有色人種」都是「虛弱的種族」。戈比諾對人類的分類就如同其他種族主義者一樣出自於偏見,只不過在血統混雜化這點上,他對人類社會抱持著一種悲觀的態度-意即混血會造成人類的退化,而且勢不可逆。 戈比諾的論調深深影響了著名的反閃族者張伯倫(Houste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這位戈比諾學會成員以及身為音樂家華格納的女婿,在西元1899年出版了十九世紀的基礎(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這本書為路線眾多不一
的反閃族和種族主義信眾提供了「理論基礎」。他說:屬於純種種族的人具備一種「特別的」-也可說是「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混血會造成種族退化。 張伯倫的論調最大的矛盾之處在於,他認為最高等的種族應該經由混血產生,即一種高貴化的過程,同時又強調只限於特定的、條件限制的混血過程才對一個種族的高貴化與新生有益。這種特殊的混血過程必須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進行,之後必須馬上停止,以免持續的混血導致種族退化。結果,他的論調一直在混血退化與種族改進之間的矛盾中擺盪。 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27)的主張與張伯倫相同,他結合文化上及生物上的觀點,認為國家也
僅在作為種族存續的工具時才有意義,而種族之間也不存在所謂的平等,甚至各具備了較優秀或者較低劣的價值。希特勒將人類分為三類:文化創造者、文化傳承者和文化毀滅者。亞利安人屬於文化創造者,東亞民族為文化傳承者-傳承自亞利安民族,而猶太人則為文化毀滅者。 2.4 優生學的起源及發展 優生學可溯及至達爾文的表弟高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可算是優生學的創建者。優生學的基本論調在西元1869年時由高頓發表的天賦的遺傳(Hereditary Genius)而建立。隨後在西元1883年出版的人類機能與其發展調查(Inquir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中,他定義-優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改善種族後代品質的學科,也就是說研究如何發展種族最大效益。 對高頓來說,優生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發展遺傳生物學的知識、研究出最適宜的生活條件以及提升一個種族整體的身心狀況。至於如何達成,他說:讓健康的遺傳傳承下去或阻止不健康的遺傳。 以英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為例,他認為,若是勞動的中產階級能比下層階級產下更多的後代,必能使種族的素質提升,在這裡所謂的下層階級指的是酗酒者和罪犯。許多英國的協會和組織團體普遍認同這種想法,並且訴諸政策上的實踐,而後也開啟了優生學運動
的濫觴。某些像「淘汰」、「優質種」、「種族純淨」的觀念均可在高頓的著作中看到,他甚至認為血統污化和文化的墮落習習相關。優生學發展到後來,凡是不合乎典型的「強勢者」或「健康的人」都被視為遺傳缺陷。更別說那些身患遺傳疾病或者行為態度不符合「理想模範」的人。所謂健康遺傳評鑑根本是對人的價值的一種簡約化評斷。 高頓談到對「低下人民」的排除,他建議「消滅」他們可以作為一種合法手段,同時,這方式亦會帶給人類文化「具有好處的後果」。在高頓的書中他對黑人是如此描述的:我們認為笨的人當中黑人佔大多數。在每本談到美國黑人僕役的書中充斥了多的是這樣的例子。他們在工作中犯的錯是如此的愚蠢、幼稚,身
為人類我自己都覺得丟臉。 高頓運用了自然科學的印證方式支持他自己的論點、描述其他族群的個別特徵。他還建議設計體態特徵測試及成立人類學實驗室,藉此紀錄視力、聽力、反應靈敏度和辨色力。總的說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高頓對人體特徵上的數據描述具有高度的興趣,並且在他的優生學觀點中佔有重要的基礎。 3.0 優生學學科的建立-西元1933年前,德意志帝國的社會、健康政策。 3.1 概述 20世紀初期德國的優生學運動蓬勃發展,除了有各式各樣的刊物發行外,更成立了學會,像是Gesellschaft fuer Rassenhygien
e、Gruend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er Bevoelkerung等。甚至從西元1920年起,德國的大學、技術學校還開設優生學課程,一般社會大眾還不時可以接受到展覽、演講、廣播節目及電影的宣傳。經過各種形式的宣傳終於引發大眾對優生學的興趣,再加上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社會上出現了不少激進的言論和要求,舆論要求刪減疾病防治措施經費以及制定身心障礙族群的繁衍禁令,也就是進行絕育手術。這些訴求種下了西元1933年納粹政權所頒布的遺傳病後代防止法(Gesetz zur Verhue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的前因。
而第一項由國家(威瑪共和國)支持通過的優生學措施其實要算是西元1926年的婚姻諮詢(Eheberatungsstellen),也就是說,未來的夫妻應該接受優生學者的建議(例如伴侶選擇)。優生學的信奉者相信在這樣的措施施行後,必能阻擋民族的沉淪,並且拯救德國民族。 3.2 優生學者主要代表人物:夏邁爾(Wilhelm Schallmayer,1857-1919) 及卜羅次(Alfred Ploetz,1860-1940) 3.2.1 夏邁爾 夏邁爾跟高頓一樣將達爾文的演化論運用在社會的發展上。他的論點主要著眼在民族的繁衍政策和民
族優生學上,夏邁爾認為此二者攸戚相關。國家在優生學政策上要特別注意對早婚的要求、兒童津貼,減少職業婦女以及多產家庭住所的擴建。夏邁爾雖然不像其它優生學者一樣著重所謂北方種族優越的論調和以醫學評鑑為主的優生學,但是他也擁護納粹所謂的民族體意識,因為他強調個人在婚姻上和繁衍上的利益不應該大於國家未來的利益。 3.2.2 卜羅次 卜羅次可說是優生學思想的先鋒,他的優生學思想主要分為兩種:一為私人領域的優生學,一公眾領域的優生學。在私人領域方面他要求個人健康狀況的提昇;公眾領域方面則注重社會的整體健康,而終極目標為達到優生學的烏托邦。卜羅次建議以「挑選方式」以達
成此目標。 一個種族的生命歷程是「變異」、「生存競爭」和「繁衍」。這個進程說明了種族如何達到烏托邦的路線。卜羅次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實現這理念的方式:一對年輕的夫婦在結婚之前應作婚前檢查,以便測知這對未來的父母在智能上和道德上的品質,同時也決定他們後代繁衍的數量。在科學態度的的照護下生產出好的(健康的)後代,其後代也要處在縝密的照料之中。所有對下一代的照料須在維護種族健全的前提下進行,若有孱弱或肢體不健全的小孩,應該「給予一劑嗎啡促使他們溫和的死去」;另外諸如疾病、失業保險或對孱弱者的醫療照護應該停止或者減至最低,因為醫療干預天擇機制。如此一來,經過各種計畫和安排便能使一個種族
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 3.3 從種族主義迷思到優生學 納粹的優生學概念根植於兩種意識形態淵源,一為遺傳健康照護,一為種族血統維護。納粹政權於西元1933年制定了遺傳病後代防止法以實現遺傳健康照護的理念;接著在西元1935年通過德意志民族遺傳健康保護法,此兩條法律合法化對遺傳病患者進行绝育的優生措施,光是西元1935年到西元1945年的10年間便有36萬人遭受此項手術,也因為這兩條法律促成了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滅絕無生存價值生命」的措施。溯及這些法律合法通過的原因,可以從對理論的誤解、誤用及某些偽科學的興起探討之:像是達爾文的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日
爾曼主義、亞利安狂熱、民族意識以及所謂的種族主義等等均是其思想的源頭。其中種族主義可以說是理念架構,它也是納粹世界觀合法化的主要原因。納粹認為在生存競爭和強者為王的觀點上,不僅個別的人會彼此競爭,就連不同的「種族」、「民族」亦然,特別是對需要繁衍出健康的亞利安人來說更格外重要。納粹不止看重「種族」的迷思,更進一步進行「遺傳的挑選」。希特勒在西元1934年對他的同志黨員作了以下的宣言: 為了照料這些遺傳病患,國家勢必得長期負擔持續攀升的重擔,只要這個國家持續地受到這種詛咒,它就必須設法補救,不是防止那些冤妄的負擔繼續傳承;便是要從健康的人身上取出必需品以滋養數以百萬計孱弱的人
。 這時遺傳病後代防止法業已通過,希特勒於是下達決行安樂死的命令。包括同性戀者,那些不適合社會的人特別容易受到迫害和強制绝育,因為他們不會履行繁衍的重責大任,這自然會導致民族力的衰弱並危害民族的軍事力量,所以同性戀者最後該為民族沉淪和衰弱負責,實際上同性戀者也被視為國家的敵人。當時的醫生和相關學科的研究學者其實亦投注相當的精力研究、探討同性戀議題,無獨有偶的是,不管從遺傳生物學觀點或病理學觀點,同性戀在當時均被視為一種「缺陷」。 秘密警察首領希姆樂(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在西元1937年時對這個「問題」作了以下評論:同性戀
是一種墮落,同時也是一種俱傳染性的瘟疫。同性戀會引誘他人並帶來長期的性向改變,性向改變之後會一個傳染給下一個,像是滾雪球效應一樣。我們要藉著醫學之助停止這種瘟疫。 附錄:性改革運動 第一個性改革組織是科學博愛委員會(das Wissenschaftlich-humanitaere Komitee,簡稱WHK)。此委員會是由心理學家兼社會學家賀許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與其友人在西元1897年柏林所設立,其成員多是知識份子,並且在全德國大城市均設有分會。全盛時期甚至擁有超過3000名的醫生會員。科學博愛委員會的主要目
標為推動廢除刑法第175條,為了達成此一目標,該委員會募集了包括科學家、醫生、律師、教師和作家的連署申請書。次目標則為對同性戀議題從法學、醫學、歷史、人類學諸多層面,並以普羅大眾為對象進行研究成果的發表。性改革的範圍尚包括女性地位的法律平等、墮胎合法化。定義模糊的字眼如大眾福祉、風俗習慣、民族生命體純淨等,基本上不為他們所接受。可是,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發生、議會的怠惰和納粹的奪權,這些目標終究未達成。 威瑪時期,除了科學博愛委員會之外尚有眾多其它致力於同性戀運的組織、刊物和雜誌:Bund fuer Menschenrecht(BfM)、Freundschaft、Die Fre
undin、Das Freundschaftblatt、Blaetter fuer Menschenrecht、die Insel以及Wochenschrift fuer ideale Freundschaft等超過30種不同的刊物及組織。 那個時期算是同性戀運動的一個高峰。 4.0 納粹時期對同性戀者的迫害 4.1 概論 比較不同時期的「犯罪」統計數字可以一窺不同時期對同性戀者迫害的情況。17、18世紀對同性戀行為的判刑基本上是比較輕微的,案例也少。而西元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後,相關的判決從2個星期到3個月的
拘禁或易科罰金,若是與男性性交易者或未成年者發生性關係才會判處更重的刑責。在某些狀況則是觸犯了刑法第183條-引起眾怒,也就是說在公廁、公園、果園進行性行為,而遭到警察、路人發現。一般說來,刑法第175條較少適用於同性戀者身上,反而是刑法第183條較多適用。 John C. Fout將納粹時期對同性戀者的迫害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西元1933年至西元1936年(準備期)、第二階段從西元1936年至二戰爆發(系統性的迫害)、第三階段為二次大戰時期的謀殺。 第一階段始於西元1933年11月妨害風化防止法(das Gesetz gegen gefaehrl
iche Gewohnheitsverbrecher)通過開始。此條法律主要針對反社會者,其刑責尚包括保安處分,以及規定绝育的第42k條亦適用。西元1935年,納粹進一步擴大遺傳病後代防止法的犯罪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將第14條第2款加入遺傳病後代防止法中,使得同性戀者亦負有绝育的刑責。 與妨害風化罪罪犯相比,遺傳病後代防止法把同性戀者明確地列為絕育的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之一。而約從西元1936年起,納粹政權便將絕育作為消除同性戀者的主要手段。由於同性性行為均有數個法條適用判刑,使得同性性行為在刑法上成為一項難以評估的犯罪構成要件。在第一階段約有7000人由於同性戀遭到判刑,他們
大多數是希特勒青年團、衝鋒隊和男性性交易者。從法條的改變和判刑的確定可知,納粹政權的確對同性戀者抱持不同以往的態度。 第二階段的迫害從西元1936年8月至二戰爆發。此階段可謂大規模、有計畫的迫害,納粹對同性戀者的打擊在這個階段越來越強烈,同時也把注意力投向私人生活領域中,例如從遭逮捕的同性戀者及男性性交易者身上套取交往或交易的告密名單。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同性戀者的名單是經告密的途徑取得。另一告密名單來源則為其他的家庭成員(多半是父母),因為受到當時流行的同性戀瘟疫感染理論的影響,家人擔心其未成年男孩會受到引誘成為同性戀。 令人注意的是,西元1935年刑法第
175條擴大了適用範圍與刑責,刑責加長至1年至10年,而且保安處分也改為送進集中營。很清楚地,納粹對同性戀者在法律是毫不留情的。 第三階段則為對同性戀者的屠殺。屠殺地點為集中營、療養院、監獄和軍隊緩刑營。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與位於柏林的帝國法務部達成一項協議:鑒於戰事曠時日久,優秀的德國民族在戰場上犧牲過大,因此要消滅反社會份子,以達到(數量)平衡,其方式可經由勞動-勞動至死(Vernichtung durch Arbeit)。法務部擬定了一份包括反社會份子和同性戀者的名單作為首選目標。 在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狀況混亂、或者由於資料不全、或者
資料遭到刻意銷毀,使得遭到殺害的同性戀者人數不明。在眾多研究數據中,人數統計估計由25萬人到100萬人不等。 4.2 集中營的同性戀者 每個在集中營的營囚均需佩戴三角色章以表明身分,三角色章縫於囚衣的左胸和右邊褲管上,一般刑犯佩戴綠色三角章、反社會犯配戴黑色、流亡犯配戴綠色、吉普賽人配戴棕色、政治犯配戴紅色、耶和華見證配戴淡紫色、同性戀者佩戴粉紅色,這種「系統分類」根本不是公務作業上的考量,反而是一種帶有歧視意味的機制,這是集中營有其特有的「社會階級」。除此之外,集中營囚主要還按照種族主義的觀點分為兩大類,而且待遇不同:一類為「人」,另一類為「下等
人」。來自德意志帝國、北歐、西歐、南歐的營囚地位便高於東歐人及猶太人。雖然同性戀者按照分類屬於「人」這一類,但是其地位與猶太人一樣位於最低等,被視為不正常、有害且是多餘的。 以下將舉一位從集中營存活下來的同性戀者Heinz Heger的自傳作為例子,藉以說明同性戀者在集中營的遭遇。 Heinz Heger,奧地利人,西元1939年22歲時由於觸犯帝國刑法第175條遭到秘密警察逮捕,遭判刑六個月監禁,之後並未被釋放,反而遣送至Sachsenhausen集中營。在他的營房內還有其他180位從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同性戀者。在集中營內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同性戀者是
一群最常遭到凌虐的人,舉凡繁重的和危險的工作(礦坑)都落在他們身上,甚至隨時都處在死亡的威脅中。在醫療營同性戀者也是醫學實驗偏愛的「實驗材料」(人體實驗或改變性傾向實驗),在實驗結束後鮮少有同性戀者能夠生還。 在西元1940年Heinz Heger被轉送到Flossenbuerg集中營,在那裡他成為營房管理者的性發洩對象。其實年輕的營囚(特別是年輕的男同性戀者)通常會被選為某些營區管理者的僕役兼性發洩對象,不過,諷刺的是,這樣也比較容易獲得程度上的「保護」而從集中營那種悲慘的日子中存活。Heinz Heger形容他當時被「挑走」時的情況宛如身處古羅馬帝國時的奴隸市場。
真菌微宇宙: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動世界、推展生命,連結地球萬物

為了解決安德瑪衝鋒衣 的問題,作者MerlinSheldrake 這樣論述:
真菌, 是地球上最優雅的生命策略, 也是最精細而普遍的存在。 ★2017年法蘭克福書展最受矚目重點書 ★《時代》雜誌、BBC Science Focus、《每日郵報》、《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評選年度最佳書籍 ★美國亞馬遜超過2800位、英國亞馬遜2700位讀者五星推薦 ★亞馬遜蕈菇真菌類書籍第一名、環境生態類書籍第二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張東柱審訂 每當我們談論真菌,往往都被蕈菇主宰了想像。 然而,蕈菇只是真菌的子實體(就像是果實),真正多數的真菌,都生活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隱而不顯。我們對真菌所知甚少,有超過90%的真菌不曾被人
類記錄,但卻默默地構成了一個廣泛而且多樣的生物王國,維持著地球上幾乎所有的生物系統。從海床上最深層的沉積物,到沙漠的土表、南極冰凍的谷地,甚至我們的腸胃……在這個地球上,很少有真菌到不了的角落。 劍橋大學生態熱帶學博士,梅林.謝德瑞克,是英國近年備受歡迎的生物學家,真菌是他生活上的繆思,也他是投身學術的原因,好探索這個一直存在於我們身邊,卻彷彿平行時空般隱密而龐大的世界。 或許從來沒有人這樣跟你說過,但梅林.謝德瑞克便試著要告訴你:若想要了解我們居住的星球與環境,了解我們何以如此思考、感覺與表現,真菌就是關鍵。 ◆把生命推進陸地的前鋒 在那個陸地尚未出現生命的久遠年代,是
真菌率先結合藻類,成為地衣,把生命推進焦枯荒涼的陸地。地衣破壞、分解岩石,最早的土壤隨之誕生,鎖在岩石裡的養分與礦物質才得以進入生物的代謝循環系統中。時至今日,陸地上最荒涼的土地,仍然是由地衣衝鋒陷陣,建立新生態系。 ◆植物的根本:真菌 六億年前,綠藻從淺水中登陸,沒有根系的它們藉由連結真菌,才得以輸送水分,從大地汲取養分,這是最早的植物型態。這樣久遠的聯盟,演化成現在的「菌根關係」。今日,仍有超過90%的植物種類依舊依賴「菌根菌」,這些無數的微小互動,也表現在植物的外形、生長、滋味和風味中。而科學家更發現:在森林的地底下,有一組由植物與真菌組成的神祕網絡:「全林資訊網」。 ◆
人類離不開真菌 《發酵聖經》曾提及:「某種程度上,我們吃進的微生物,決定了我們的代謝能力。」這裡的微生物,指的就是真菌。人類與真菌的關係密切,身體或腸道內的微生物,就是最好的證據。不僅如此,人類更善用各種發酵設備與真菌合作,製造出我們熟悉的酒精、醬油、疫苗、盤尼西林,或是碳酸飲料裡的檸檬酸,我們由內而外,與真菌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行為。 ◆諸神血肉:展現心靈之藥 真菌演化出來的化學物質──裸蓋姑鹼,被歸類成迷幻藥或宗教致幻劑,自古以來就被納入人類社會的儀式與精神教義中,這類蕈菇的應用,目前最早的記載發生於墨西哥,修士將這種被稱為「諸神血肉」的蕈類,呈給了加冕時的阿茲特克皇帝。這種
迷幻蕈菇可以用來鬆脫我們思想的界線,軟化心智的死板習慣,甚至,科學家發現,其中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夠減輕癌末病患的重度憂鬱與焦慮。 ◆什麼都吃!分解的大藝術家 我們現在呼吸、居住的空間,是真菌分解各種生物遺骸所空出來的空間;如果真菌停止分解作用,地球上的遺骸,足足可以堆積出幾公里深的厚度。 真菌多樣的代謝能力是化學轉換的藝術,能夠分解許多地球上最頑固的物質。木材裡的木質素,就稱得上最難分解的物質之一,但對白腐菌來說,分解卻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科學家也試圖運用真菌的好胃口,訓練它們分解菸蒂、殺蟲劑、尿布、PU塑膠與致命神經毒氣,甚至是核廢料的放射性物質——科學家發現,一種能吸收放射性
粒子散發能量的「輻射營養真菌」,就在車諾比的廢墟裡旺盛生長;而廣島在原子彈的轟炸後,據說,最先長出來的生物就是松茸。 梅林在書中描寫了自己在巴拿馬叢林等地方研究真菌的歷程,並以優美精練的文筆,探究真菌在不同時空背景、文化以及各種領域的發展(包括親自服用迷幻蘑菇的過程),同時紀錄研究真菌的學者如何交鋒,也描繪真菌在科技上帶來的驚人成就。 紮實的學術訓練,加上細膩的觀察與人文觀點,都為《真菌微宇宙》展現出更宏大的格局與企圖,也描繪出更動人的世界。最終,梅林嘗試著要讓我們理解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唯有真菌,才能將各種生命串連在一起。 「我們活著,都在呼吸真菌! 真菌造就世界,
卻也能夠瓦解世界。」 名人推薦 胖胖樹 王瑞閔/植物科普作家 董景生/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組長 蔡怡陞/博士、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謝廷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組長--共同推薦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各界好評 「質感亮眼的初試啼聲之作……從麵包到酒,到構成生命的質料,這世界繞著真菌打轉,而梅林.謝德瑞克為我們做了一流的描繪。」──《科克斯書評》 「深具啟發地探討真菌,證明真菌和人類的關聯遠遠不止於用在烹飪中……(《真菌微宇宙》)是對另一個生物界令人無比享受的讚歌。」──《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非凡之作令人愛不釋手,探索了真菌驚人的活躍範圍──讓生命登陸陸地;以無數的方式和其他生命形態互動;塑造了人類歷史,甚至可能保衛我們的未來。《真菌微宇宙》既嚴謹科學,又大膽想像,提出了關於地球生命各種特質的一些根本問題。」──尼克.賈丁(Nick Jardine),劍橋大學科學歷史與哲學名譽教授 「《真菌微宇宙》是梅林.謝德瑞克的傑作,既學術又有創見,並且引人入勝,讀來享受。這本書為生物的真菌界提供了極具洞察力的新分析,所有生物領域的學生讀了都會獲益良多。」──伊恩.韓德森(Ian Henderson)博士,劍橋大學植物學講師 「真菌令人著迷!優雅的生命策略加上精緻的普遍存在
,驅動了全球的生態系。謝德瑞克的書中極富教育意義,提供了新觀念。透過謝德瑞克的目光來看,真菌學與藝術、哲學和人類社會融為一體。謝德瑞克的筆法真實而私密。他的書有趣又有教育意義。」──烏塔.帕茲科夫斯基(Uta Paszkowski),劍橋大學植物分子遺傳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