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吳永華寫的 馬偕在宜蘭:日記、教會與現場 和吳永華的 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白象文化 和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所出版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李文環所指導 黃雅婷的 壽山植被變遷之歷史研究 (2020),提出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壽山、植被、自然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許佩賢所指導 賴俊諺的 日治時期公學校校園空間的利用與農業實習教育 (2019),提出因為有 學校園、農業實習地、學林地、公學校農業科、勞動實習、感官規訓的重點而找出了 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的解答。
馬偕在宜蘭:日記、教會與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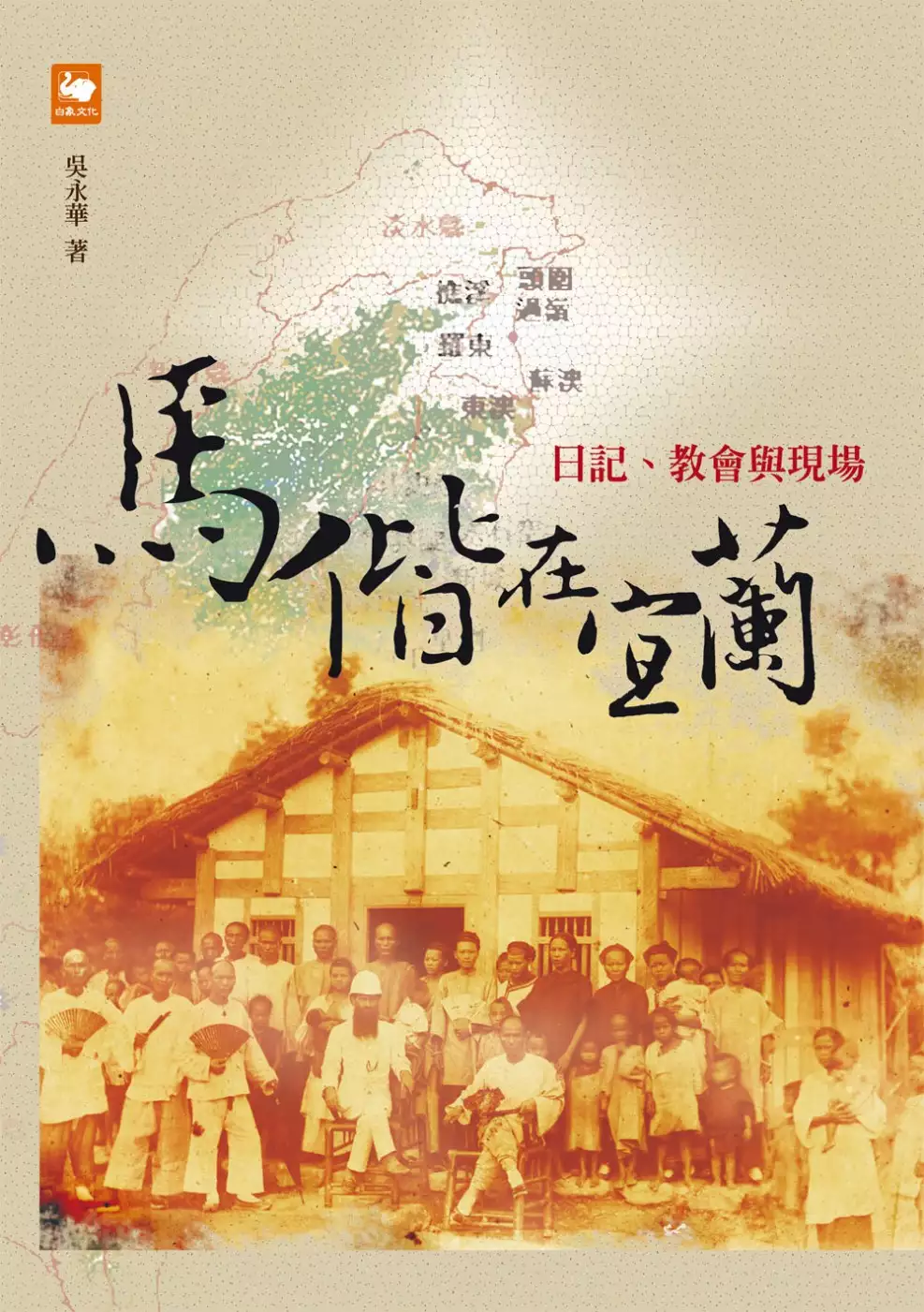
為了解決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的問題,作者吳永華 這樣論述:
囊括28次旅行路線、宣教內容及其所建立的35所教會, 一部完整、精實的馬偕在台巡醫田野調查記錄。 ◎8條跟隨馬偕巡醫的自行車旅行路線,一邊享受郊遊休憩的小確幸,一邊體驗重回歷史現場的感動。 ◎囊括28次旅行路線、宣教內容及其所建立的35所教會,一部完整、精實的馬偕在台巡醫田野調查記錄。 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馬偕博士,於19世紀後期至台灣傳教與行醫。 由1873 年10 月21直到1900 年5 月26 日,馬偕到訪當時貧瘠落後的蘭陽平原行醫次數共達28 次之多,在宜蘭的停留總天數超過300 天,達十個月以上。 除了在自宅展開免費醫療的工作,教導民眾公共衛生知識,
為人拔除蛀牙,贈送虐疾特效藥,治療腳膿瘡(俗稱臭腳粘),並由國外輸入蔬菜種子如蘿蔔、甘藍菜、蕃茄、敏豆、花椰菜、胡蘿蔔等,介紹給農民種植。更於1880年在滬尾(今日新北市淡水區)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醫院——偕醫館(馬偕紀念醫院的前身)。 馬偕常常和助手旅行佈道,深入平埔族、熟蕃、南勢蕃、生蕃居住的村落,隨時在路邊幫人拔牙,曾在日記上記載他昨天拔了多少牙,今天又拔了多少牙,終其一生,馬偕總共為台灣人拔了超過兩萬一千顆牙。 本書根據《馬偕日記》、《北臺灣宣教報告》等教會史料,整理馬偕在宜蘭的28次旅行路線、宣教內容及所建立的35所教會,進行田野調查,尋訪舊社位置,並規劃緬懷馬偕的宜蘭
小旅行。提供讀者重回歷史現場時的知識依據,與馬偕心靈交會時的連結線索,增添閱讀與禱告的養分,進而激發再生的力量。
壽山植被變遷之歷史研究
為了解決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的問題,作者黃雅婷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研究壽山植被變遷的歷史。壽山是我國的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國家自然公園。本區面積約1,100公頃,植物生態豐富且外來種比例高。北壽山(龍泉寺)、中壽山(礦區)與南壽山各步道相距不遠,但植群型態變異很大,如此獨特的植物景觀究竟如何形成?其植被變遷的歷史令人好奇。文本中的壽山最早可追溯到荷蘭時代,當時是林木與蘿藤的產地,推測應該植被繁盛才能持續供給輸出。清代則是在地民眾獲取柴薪的「柴山」,柴薪由輸出轉為自給,此時期林產物逐漸衰竭,當清末西方旅人到來時已是嶙峋禿山。日治時期壽山因臨近開發「打狗市區」的計畫地點,為了保障市區安全,1907年成為臺灣第一座公告的保安林,肩負國土保安與水源涵養
重任。1908年打狗市區改正後,眺望景觀良好的東南角山腹被規劃為「打狗公園」。此時壽山仍是童山濯濯,臺灣總督府於1908年從壽山南側開始造林。1908~1920年「打狗公園」時期造林首重「快速成林」,樹種選用速生型經濟樹種,以水土保持及經濟效用為主,市郊公園的景觀角色則不重要。1923年裕仁皇太子行啟高雄後,壽山搖身成為承載殖民教育使命的「壽山紀念公園」。1925年本多靜六將其規劃成為一座複合式遊憩聖地,造林目標轉變為「創造花山景致」及「培育熱帶果樹」等景觀營造及遊憩體驗。樹種選擇以開花樹種為主,乘載日本生活慣習與文化,並融入南洋的異國風情,形成彰顯公共空間與殖民地教育的文化地景。1937年日
中戰爭爆發後,配合南進政策,壽山劃入「高雄要塞管制區」,成為掌控港口、海域與防空的軍事重地,自此斷絕與民眾的連結。軍事管制打亂了原本的造林計畫,降低人為干擾,使當時尚未造林的北壽山自然演替成為生物多樣性高的天然闊葉(次生)林(而非如南壽山一般生物多樣性低的人工闊葉林),埋下未來成為國家自然公園的契機。戰後部分山區逐步開放為「壽山公園」。1992年聯合國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簡稱CBD),乘著國際的保育熱潮,時值壽山東側的臺泥採礦權期滿之際,在地方民間團體奔走下,「壽山公園」成為我國第一座「國家自然公園」,開啟「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的新使命。壽山紀念公園規劃者—本多靜六的觀點:「一個地區
的林相,反映了此區域的文化歷史。」壽山現在的四大種類植物社會:「天然闊葉(次生)林」(北壽山)、「人工闊葉林」(南壽山/壽山紀念公園)、「人為破壞地綠化植生」(臺泥礦區)及果園(人工闊葉果樹混合林),此四種不同的植被型態,係由「文化力」和「自然力」共同塑造,反映出此區域歷史的縮影。
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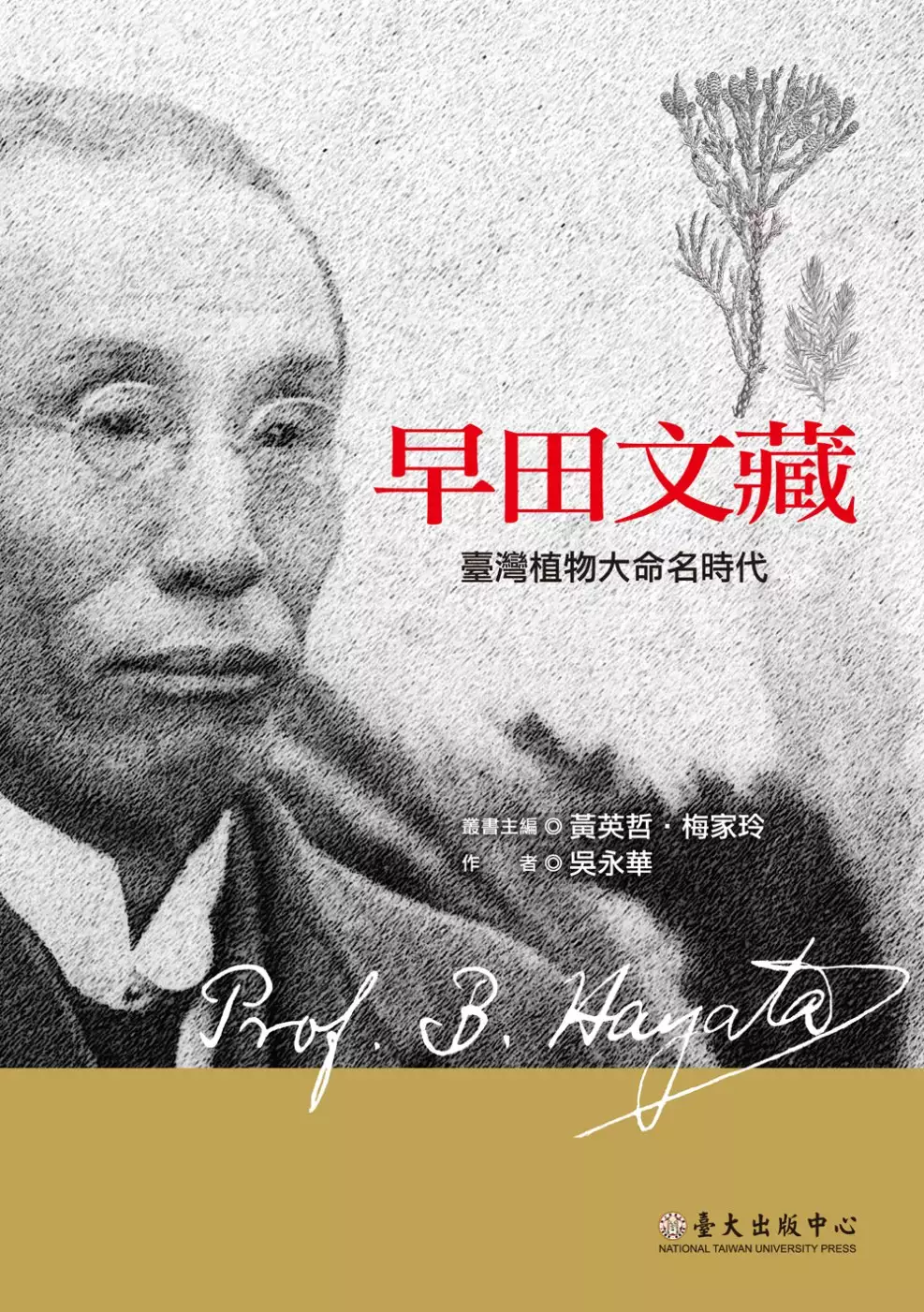
為了解決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的問題,作者吳永華 這樣論述:
早田文藏, 他是享譽國際的「臺灣杉」的命名者, 也為臺灣建立8個新屬、1,636筆新學名, 他的一生,成就出近代臺灣植物學的輝煌年代。 早田文藏(1874~1934),日本新潟縣加茂町人,16歲矢志於植物學,1892年19歲加入東京植物學會。1903年師從東京帝國大学理学部松村任三教授後,接手臺灣植物研究。1905年受聘為臺灣總督府植物調查囑託,直到1924年為止,十九年間致力於臺灣植物的研究與分類,完成《臺灣植物圖譜》十卷。由早田文藏命名發表的臺灣植物多達1,636筆,被譽為「臺灣植物界的奠基之父」。 本書透過早田文藏的生平歷程,闡述他身處的大時代環境,是如何
引發他對植物學的喜好,並在因緣際會下進入臺灣植物研究的領域,成為建構臺灣植物誌的重大功臣。他一生關注分類學、形態學、解剖學、細胞學等植物學議題;晚年更涉獵宗教、哲學等層次,進而提出新的「動態分類系統」,影響無數後世學者。一部早田文藏的傳記,講的不只是一位先驅者的生命歷程,更是臺灣自然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頁。 本書特點 ●補足日治時代臺灣自然史的一塊重要拼圖。 ●臺灣第一本早田文藏詳實傳記,呈現早田文藏一生的成就事蹟。 ●整理早田文藏一生著作目錄及命名一覽表,是研究臺灣植物史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聯合推薦 許再文(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植物組組長) 郭城孟(臺灣生態旅
遊協會理事長) 黃裕星(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所長) 楊宗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組研究員) 劉克襄(詩人、自然生態保育工作者) 鍾國芳(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名家推薦 早田文藏在1911年出版的〈臺灣植物資料〉中發表了新種山薰香,並註記道:「……在福爾摩沙所有的植物中,或許最令人震驚的發現就是山薰香屬了,此繖形科的植物除了臺灣之外只分布在澳洲,本屬不僅是臺灣島的新物種,也是北半球的新紀錄。」在二十世紀初臺灣植物大命名的時代,要在高山聳立的福爾摩沙發現新種植物並非難事,但能發表北半球新紀錄屬,並評論其世界地理分布,這讓我在博士班研究山薰香屬生物地理時,對早田
氏這位將臺灣植物學推上世界舞臺的日本植物分類學者更多了幾分敬意。吳永華先生所著《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鉅細靡遺的考據了早田氏的生平與他在臺灣植物分類學的卓越貢獻,深入剖析了其著作中極具爭議的蕨類中心柱構造、動態分類系統理論,與森丑之助對其嚴厲的批判,讀此書我彷若被帶回到上世紀初臺灣植物分類研究最精彩的時空,多年的疑惑也在此書中一一開釋,欲罷不能。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鍾國芳 自然誌研究是條孤獨的長路。多數人可興發一時之趣,或以本身學術範疇之必要做階段性的爬梳。作者非科班專業,卻堅持一已之信念,沿此路徑壯遊,愈往偏僻之區披荊斬棘。長期的基礎調查,反而超越現有研
究者的成績,更成為我們回顧過往的重要指引。 透過早田文藏生平的認識,無疑是了解日治時期臺灣植物調查和研究的重要脈絡。百年前這位植物學者在臺灣的種種調查和經歷,如今重新建構,勢必得需要花費更多苦功,逐一拚圖補文,才可能在生硬粗疏的史料裡,給予豐厚的表述。 若沒作者的執著傻勁,日治時期的自然人文勢必少了一大塊。回顧這條臺灣自然誌的小徑,瘦長而彎曲,草木蔚然茂密,幾無後繼者。走進去,或走過都是沒有掌聲的,縱使到了盡頭,仍只有孤獨的巨大寧靜。但作者繼續向前。 ──詩人、自然生態保育工作者 劉克襄
日治時期公學校校園空間的利用與農業實習教育
為了解決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的問題,作者賴俊諺 這樣論述:
自日治時期近代學校成立以來,校園風景中便開始出現花圃綠樹等植栽。這些植栽除了造景功能外,也被總督府作為培養農業技術的教材,運用於農業教育實習課程中。本研究旨在探討公學校普遍設置的學校園、農業實習地以及學林地三項設備的成立過程,透過法規規範、教育期刊以及公學校檔案釐清其教育活動與意義。「學校園」可包括學校中各植栽與畜牧園區。明治38年(1905)臺灣教育界開始討論「學校園」的設置,逐步定位出培養「美的感知」、「勤勞道德」,以及作為「理科直觀教材」、「實驗作物」的功能。其中,「實驗作物」為透過栽植實驗以改良在地作物,與嘗試種植自南洋等地引進的熱帶植栽。「農業實習地」與「學林地」則是配合農業實習課
程的園地,此二類園區的設置,對於公學校而言具有從收穫獲得「經濟效益」的功能性。1930年代,學校園等設備轉為強調「愛國奉公」,實習地配合祭祀活動及奉公獻納;校園植樹與學林地,積極配合愛林運動的實施。進到戰爭時期,甚至打破原有課程設計,整片農業實習地改作必勝蓖麻園,完全成為國家供應前線軍需的場所。對於統治者而言,學校空間是有別於教科書的工具,透過視覺與勞作教化引導學生符合統治的教育理想。政權轉移之後,校園農業教育的性質褪去,存在的造景仍舊保存著美感視覺規訓,以及等待被賦予新教育指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