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美)列斯特·坦尼寫的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 和余先予等的 東京審判(第三版)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重慶 和商務印書館所出版 。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班 林桶法所指導 李一鳴的 日本侵華時期「滿洲國」的意象與反思 (2019),提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滿洲國、溥儀、滿清遺臣、日本、關東軍。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劉維開所指導 蕭李居的 防共議題與中日關係(1931-1945) (2018),提出因為有 防共協定、蔣介石、汪政權、中蘇關係、日蘇中立條約的重點而找出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的解答。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

為了解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 的問題,作者(美)列斯特·坦尼 這樣論述:
本書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征集資料,結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二戰期間,守衛巴丹的美菲聯軍在彈盡糧絕之后被迫投降。日軍強迫這些精疲力竭的戰俘長途行軍。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日軍隨意呵斥、抽打、屠殺戰俘,慘無人道。在被送到日本福岡縣大牟田17號戰俘營后,坦尼和同伴被迫深入地下采煤。他冒着生命危險,利用日語能力和交際手腕,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地下交易網絡,與日本看守和礦工做生意。地下市場的主要流通貨幣是香煙,價值最高的
交換物是米飯,戰俘們的牙膏和鞋子很受日本人的歡迎。坦尼細膩的筆調,讓讀者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日本侵華時期「滿洲國」的意象與反思
為了解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 的問題,作者李一鳴 這樣論述:
滿洲國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其政體上的改變。滿洲國建國初期是執政擔任元首的體制,到後續改變成了帝制,將國號變為大滿洲帝國。從滿洲國到大滿洲帝國的過程中,溥儀也經歷了從滿洲國執政到大滿洲帝國皇帝的身份變化。它的特殊之處還體現在,正如法國的路易十六一般,溥儀是共和國推翻的君主,當時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共和國時代,而他卻又擔任的共和國的元首,這對於已經進入共和時代的中國國民來說,不禁要問「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共和」?似乎是歷史中很令人不解之處。因此滿洲國的探討始終是被人關注的焦點。本文將探討滿洲國成立前後,參與其中的部分群體對於滿洲國建立前的憧憬以及對於建立過程與解體後的
反思。並通過對歷史資料分析,闡述文章的主角隨著時間的改變,態度與思想是否保持亦或有所變遷?本文的主角有三:滿洲國皇帝溥儀、滿洲國大臣——以個別人為例、滿洲國的幕後主人——日本關東軍。分別通過這三方的視角來剖析滿洲國的意象與反思。 本文共三章,第一章是從意象角度出發,分別從主角們的立場——日本、溥儀、滿清遺臣探討與研究各自對於滿洲國的意象。第二章是利用當時的報紙與文字資料的記述,探討各方對滿洲國的成立的態度與應對。第三章是反思,同樣的探討三位主角在建國初期與解體後兩個時間節點的反思。並且在最後總和三章的討論,在經過一系列的研究與探討後,得出相應的結論。
東京審判(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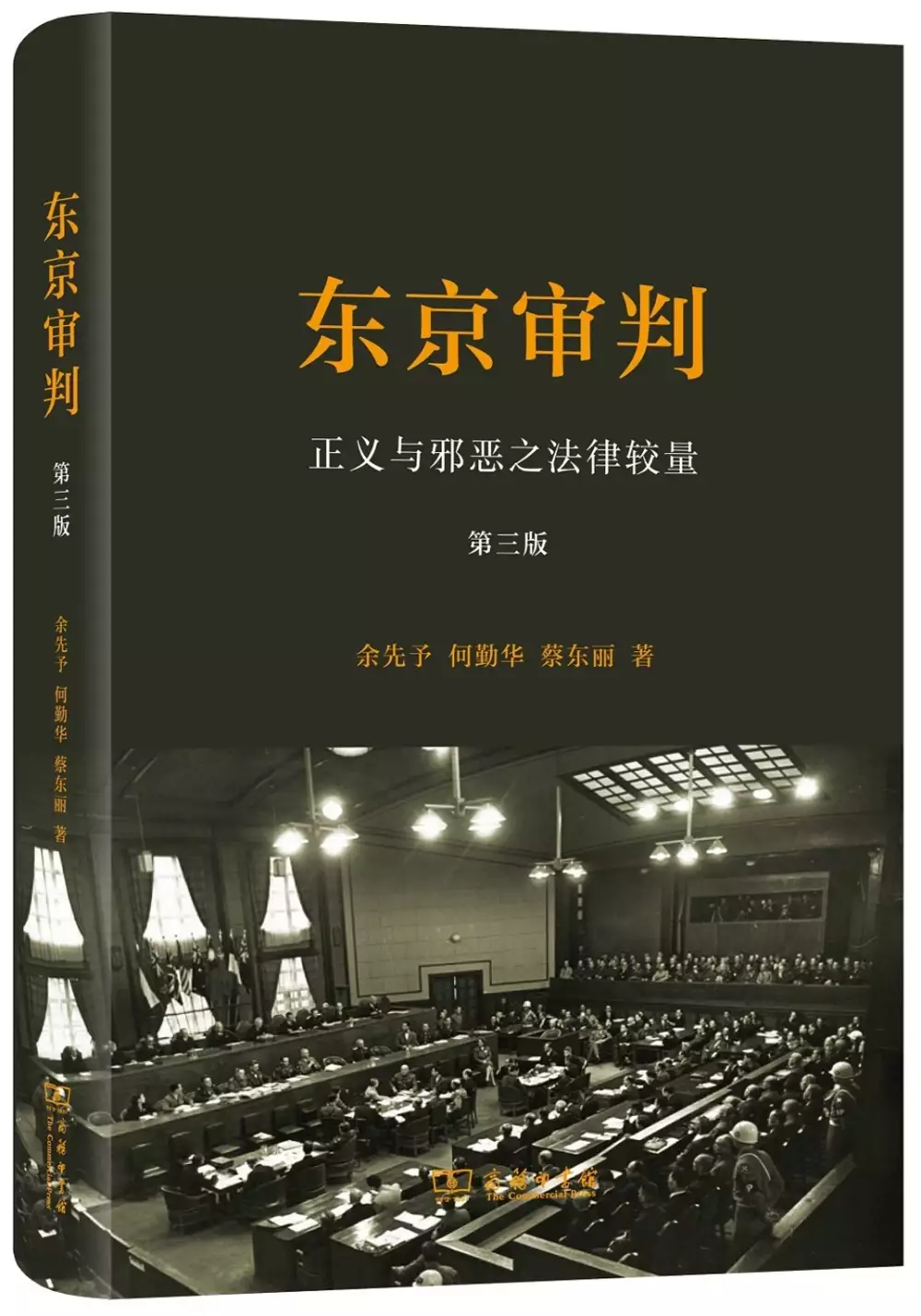
為了解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 的問題,作者余先予等 這樣論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從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東京進行了歷時兩年零六個月的「世紀大審判」。來自同盟國11國的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清算戰爭罪行的審判。歷經818次開庭,法庭證實了日本甲級戰犯所犯罪行罄竹難書:在日本國內利用新聞檢查制度、警察鎮壓體制向人民宣傳對外擴張計划,大力推行軍國主義政策;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扶植「偽滿」、發動「盧溝橋事變」、制造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等;積極建立軸心國同盟;侵略東南亞諸國;偷襲珍珠港……東京審判本身面臨哪些法律困境與挑戰?審判團如何克服辯護方基於英美訴訟程序規則實施的拖延策略?能否對
發動戰爭的領導、策划和實施者追究個人刑事責任?……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法律較量。本書一一為您呈現。余先予,湖南長沙人。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出版《沖突法》《國際法律大詞典》等多部作品,發表論文100余篇。1994年英國劍橋傳記中心授予20世紀成就獎、美國傳記協會授予國際傑出領導者獎。曾任港澳台經濟與法律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何勤華,上海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前任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着有《西方法學史》《20世紀日本法學》《中國法學史》等多部作品,在法學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180余篇。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1992年起享受國務
院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獲第二屆中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稱號,2009年獲「教學名師」。兼任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2015年7月任中華司法研究會副會長。蔡東麗,湖北孝感人。法學博士。出版合着《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國古典法學名著選讀》等,在各類公開刊物上發表論文十余篇。現任教於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
防共議題與中日關係(1931-1945)
為了解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判決書 的問題,作者蕭李居 這樣論述:
過去已發生的歷史事實並無法改變,但如何理解、解釋與認識歷史,並非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對於1931年至1945年期間中日糾紛與戰爭的歷史本質,若只是理解為強權國家侵略弱國的單一觀點並不適切,應該要深入釐清中日的國家發展及彼此關係發展的困境。而在考慮中日外交與戰爭的歷史性格,防共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觀點,更是兩國關係惡化與陷入長期戰爭的主要根源。就防共所指涉對象而言,包含共產主義、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共等不同概念。日本的防共概念主要為對蘇備戰,在推動對華外交加上防止共產主義滲透,即主要以此二者為目標。但戰前中國方面因為內部國家統一問題,國民政府的防共概念基本上以中共為對象展開武力清剿。雖然同為防共
,但概念的不同與目的的差距,在對話基礎上已經難以同調,若欲合作防共當會有一番折衝拉扯與對抗,導致九一八事變惡化的中日關係雪上加霜而引爆戰爭。即使在日本與臨時政府及汪政權等附日政權合作防共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現日「華」雙方的防共概念不盡相同。日方的概念基本上主要仍是以蘇聯為對象,附日政權則為共產主義與中共。惟雙方並未仔細或者不欲釐清此種差別,並在占領區的治安問題下,共同防共的結果反而符合附日政權以中共為對象的防共概念。重慶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並未放棄以中共為對象的防共概念,而日軍在華北與華中戰場已與附日政權合作剿共,但重慶方面因為主權與民族主義問題以及中共高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還有美蘇勢力
藉由戰爭進入影響中國內部的國際因素等,都使得重慶方面不可能放棄抗日政策而改以與日本合作武力剿共,因此重慶主要仍是採取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防共概念。結果不論是戰前或戰爭期間,中日雙方都難有合作防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