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a bid to意味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Woolf, Virginia寫的 A Room of One’s Own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楊昊所指導 黃以樂的 甚麽是親中?中國-馬來西亞關係近況發展的6M分析(2013年-2018年) (2021),提出in a bid to意味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馬來西亞、中國、中馬關係、國際關係理論、6M分析法。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王文宇所指導 林鈺棋的 公司目的變革對董事會多元化的影響趨勢—以美國為中心 (2021),提出因為有 公司目的、股東利益優先、企業社會責任、利害關係人主義、董事會多元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in a bid to意味的解答。
A Room of One’s 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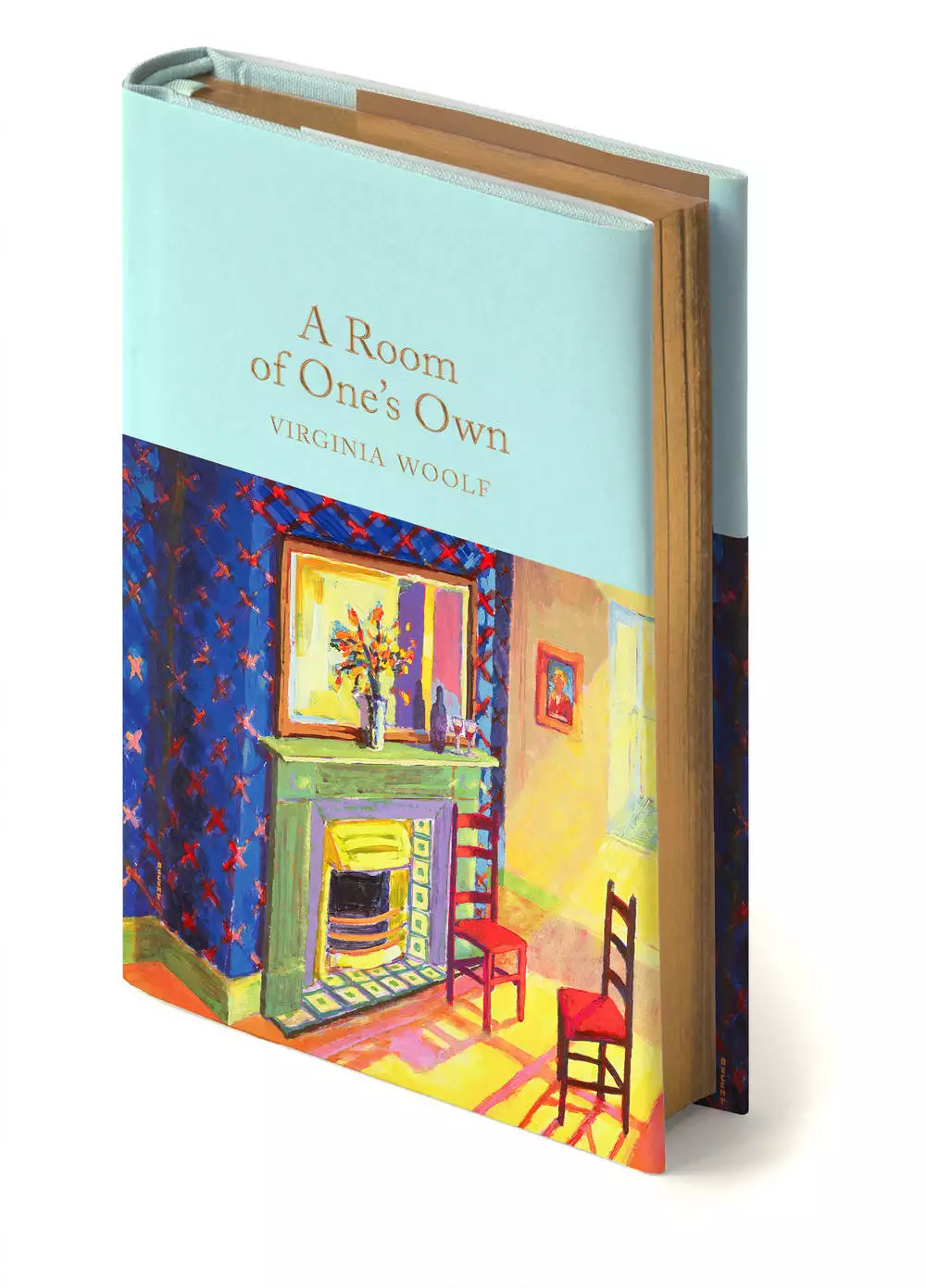
為了解決in a bid to意味 的問題,作者Woolf, Virginia 這樣論述:
女性若是想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 ——維吉尼亞.吳爾芙 Thinking is My Fighting. 吳爾芙帶領我們找回女性創作與雌雄同體的身影, 預言莎士比亞的妹妹就在你我身旁出現! 《衛報》、《時代雜誌》百大非文學作品+《世界報》20世紀百大書籍 她的質疑為全世界女人打開了改寫歷史的空間, 並激發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熱潮。 《自己的房間》是由吳爾芙的系列演講稿匯集而成,被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文學、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經典。 1928年10月,吳爾芙受邀到劍橋大學紐南學院和格頓學院兩個女子學院,就「女性與小說」的主題發
表演說。她虛構了一位當代女子的日常遭遇,包括赴大 學學院卻被斥喝遠離草坪行走,側身男性學者餐會間的被剝奪感,在大英圖書館瀏覽書架發現盡是男性作品,在倫敦公寓俯瞰街景懷想獨立女性身影等。在男性主導 的文學與學術傳統中,女性沒有自己的房間,沒有教育、經濟與社會資源,要想創作甚至在文學史上留名,實是難上加難。 吳爾芙想像,十八世紀的莎士比亞如果有位才華洋溢的詩人妹妹,她只能無名而終;而十九世紀以寫作聞名的勃朗特姊妹和喬治.艾略特,則必須以男性筆名發表,喬治.艾略特更因為與情人的關係不見容於社會,必須隱居鄉間。 「女性若是想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吳爾芙呼籲,女性擁有一個實體的空
間,繼而成為心靈的空間、思考的空間、創作的空間。在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以降的保守氣氛中,甚至對二十世紀以來女性主義的開展,都是鏗鏘有力的發聲! *此中文簡介取自>由漫遊者文化出版 In this extraordinary essay, Virginia Woolf examines the limitations of womanhoo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startling prose and poetic licence of a novelist, she makes a bid for freedom, em
phasizing that the lack of an independent income, and the titular ‘room of one’s own’, prevents most women from reaching their full literary potential. As relevant in its insight and indignation today as it was when first delivered in those hallowed lecture theatres, A Room of One’s Own remains b
oth a beautiful work of literature and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women and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This Macmillan Collector’s Library edition of A Room of One's Own by Virginia Woolf features an afterword by the British art historian Frances Spalding.
甚麽是親中?中國-馬來西亞關係近況發展的6M分析(2013年-2018年)
為了解決in a bid to意味 的問題,作者黃以樂 這樣論述:
2013年至2018年之間,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關係可謂是達到了新高點。在此期間,中馬兩國在許多面向展開合作關係,包括軍事、經貿、教育及文化等等。雙方的合作關係甚至成為了馬來西亞2018年全國選舉的重點議題之一,當時執政者以首相納吉.拉薩(Najib Razak)為首,其發起或支持的許多中馬合作工程案備受質疑,被批評是「親中」的表現。其中一個大力批評納吉親中的群體為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而他們於2018年全國選舉中的勝利無意間也被刻畫成「反中派」的勝利。整起事件的過程中,「親中」的使用似乎是貶義用途。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開始時,馬來西亞普遍華裔也高度關注此
事,而「親中」與「反中」逐漸成為了嘲諷意味極重的政治標籤。馬來西亞在2013年至2018年之間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似乎也被貼上了一樣的標籤。甚麼是親中?本研究認為目前「親中」作為形容詞的用法帶有犧牲自主權,並妥協自身立場的含意。中馬關係中是否真的有如此現象?現今有關兩國互動關係的理論架構,主要以「遠近」為衡量單位,或是以國對國之反應來判斷其關係之本質,如:新現實主義中的「抗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或「避險」(Hedging)。然而,由此角度並未能充分解釋「親中」,因為這些理論主要以國家行為者(state as actor)為衡量基準,缺乏了深入到社會層級互動
之考量。國家行為者制定決策的考量主要以可衡量之客觀元素,如:國家之硬實力(Hard power),但「親中」的表現似乎有意忽略此元素,以「偏好」(preference)作為制定決策之基本考量,社會行動者(societal actor)也因此是探討「親中」之定義重要的研究對象。本研究嘗試以Andrew Moravscik所提出的自由主義理論架構,結合Chia-Chien Chang及Alan H. Yang所提出的6M分析法,對中馬在2013年至2018年之間的互動過程進行分析,並以此探討「親中」之定義。馬國社會中第二大族群就是具有「中華情結」之華裔群體,馬國的「親中」表現極有可能由此開始。但本
研究發現馬國「親中」的表現除了源自於華裔社會行動者,也可能從處在執政層級之巫裔社會行動者。本研究以6M分析法歸納出2013年至2018年之間重要的「親中」事件,並總結出兩大「親中化」過程,即「由上至下」(國家行為者至社會行動者)以及「由下至上」(社會行動者至國家行為者)。
公司目的變革對董事會多元化的影響趨勢—以美國為中心
為了解決in a bid to意味 的問題,作者林鈺棋 這樣論述:
公司目的的論辯源遠流長,眾所周知者為1930年代兩位學者間的筆戰,時至今日,企業究竟應為何人經營一題仍莫衷一是,學者嘗試提出不同理論,有論者提出「股東利益優先」,有論者認為應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論者提倡「利害關係人主義」。商業界態度似乎較為一致,縱商業活動多樣,其間差異性與對企業宗旨之訴求不同,然觀察具代表性之美國商業圓桌會議在1997年之聲明,似可認大多數公司將優先維護股東利益,然2019年中,美國商業圓桌會議再次發表聲明,顯示「為所有利害關係人謀利」的觀點,此舉引起學界及商業界的關注,是否意味著傾向「股東利益優先」的公司目的天平,將往另一側傾斜?是否意味著「利害關係人主義」將重返焦點
,作為與「企業社會責任」、「股東利益優先」互相拉扯的第三股力量?「股東利益優先」、「企業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人主義」均屬抽象概念,本文將針對三種不同企業宗旨進行深入分析,後研究美國企業在聲明發表後的實質作為,從不同觀點切入進行分析,闡述當前美國公司對於公司目的立場採擇的主流意見。 公司目的與董事會多元化的要求緊密連結,而利害關係人主義尤甚,其與董事會多元化之間聯繫的關鍵概念為「平等」。本文將自法律面與市場面切入,說明美國董事會多元化近年來的相關改革行動。我國當以美國推動董事會多元化的歷程為借鑑,發展本土化策略,本文將觀察我國推動董事會多元化措施,以及企業實踐情形,並思考美國經驗可資學習之
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