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發現前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王曾才寫的 世界通史(三版) 和(英)G.R.波特的 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1:文藝復興1493-1520年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鄭和下西洋與西方人航海的比較硏究 - 澳門文化局也說明:新航路的開闢轟動整個歐洲,西方歷史家譽之為“地理大發現”,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載入人類史冊。雖然大多數西方史學著作對鄭和航海避而不談,但鄭和的航海成就並不比西方人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三民 和中國社會科學所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謝世忠所指導 李甫薇的 19,20世紀之交西南中國的東西方逢遇----兼論當代的國家回應 (2000),提出地理大發現前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19世紀、異己想像、認識系統、遊記、中國西南、獨立Lolo、建構。
最後網站Legend of Indian Spices 上下五千年的印度香料傳奇 - 南亞觀察則補充:三千多年前,來自古埃及、波斯,到世界各地貿易的商人、傳教士和冒險家,都留下世界文明一鱗半爪的文化遣產。 ... 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世界通史(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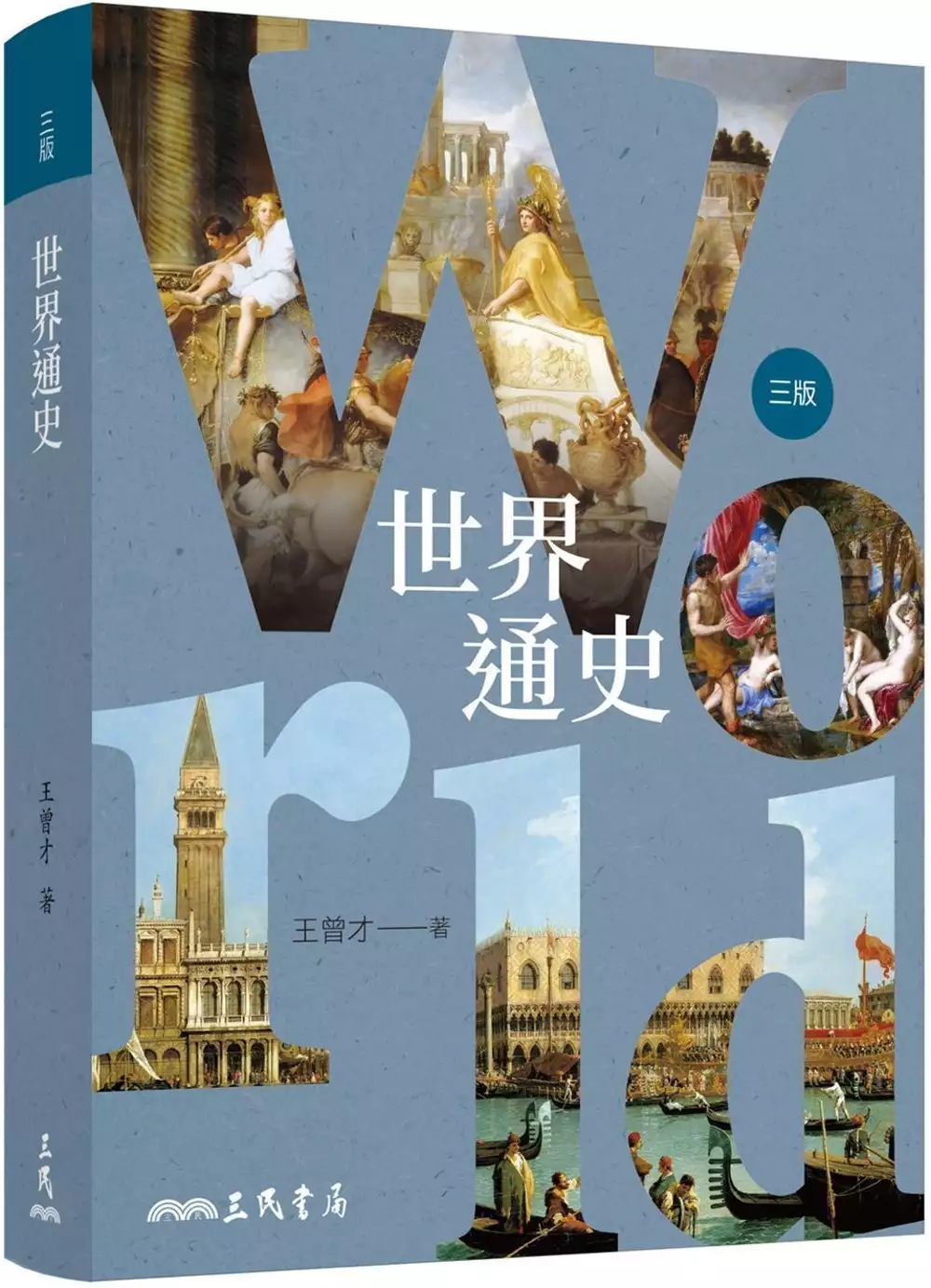
為了解決地理大發現前 的問題,作者王曾才 這樣論述:
從文明起源到列強競爭的烽火年代 一本書讀懂時代巨輪下,「一個世界」的形成!本書作者以科際整合的手法及宏觀的史學視野,用流暢可讀的文字,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敘述並分析自遠古以迄近代的世界歷史發展。內容包括史前文化、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創獲、希臘羅馬的輝煌,以及經過中古時期以後,向外擴張並打通東西航路,其後歐洲及西方歷經自我轉型而累積更大的動能,同時亞非和其他地域歷經漸變,到後來在西方衝擊下發生劇變的過程。最後整個地球終於形成「一個世界」。本書不僅可做大學教科書,亦適合社會人士閱讀。
19,20世紀之交西南中國的東西方逢遇----兼論當代的國家回應
為了解決地理大發現前 的問題,作者李甫薇 這樣論述:
在本文中,筆者以19、20世紀之交,至中國西南遊歷的西方人為對象,在人類學的歷史研究取向下,以敘述異族的歷史文獻資料如遊記、官方報告和傳教心得等為分析文本,探討19世紀異己觀念的形成,以及西方社會思潮實踐在西人中國西南論述的過程。 中國西南在漢人的眼中、一向被視為蠻夷雜處的化外之地。就漢人和西南土著的接觸而言,這裡可說是Mary Louise Pratt所指的「文化接觸區」(Contact Zone)(Pratt,1992:6)。西人自地理大發現後即積極向外探索世界,但直到1825年和1861年英法各以緬甸和安南作為殖民地時,才開始對鄰近的中國西南地
區作持續性的探險。二十世紀的泰國與雲南隔著寮國,但為了將所有泰語系小邦納入其國族-國家架構下,泰國國家領導人採用西人論述中,連結泰國與中國西南土著的歷史書寫,作為歷史教育教材(謝世忠,1993:53)。中國西南於19、20世紀之交,不但在漢人、土著、與西人的接觸下,形成一個極其複雜的「文化接觸區」,也是一個旅程與意象建構的發生地點。 西人對中國西南地區和人群的旅遊紀錄,即反應出一種對自己、漢人與土著的複雜情結。首先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提供「以基督徒來認同真正自己」的價值觀,進而發展出將他者視為異類、野蠻、化石的傳統(Pandian,1985:50)。即使十九世紀有語系、文字、體
質測量等定義人群的新指標,但這些指標仍奠基在西人的異己傳統中。在這個價值觀背景下,西人先接觸了漢人,接收到漢人對西南土著以及自己的言論,再接觸西南土著,聽到土著對漢人和自己的言論。他們遊記記載的雖然是中國西南的所見所聞,但從其選擇觀察和敘述的人事物中,仍可分析出西人建構起兩種意象,亦即分別確認了西方的優越性,以及顯示西方想在中國找尋「非中國」的企圖。除了確認優越性外,吾人也可從西人的遊記中,看出兩類反思性的論述,據此或能歸納出一個西人對中國西南的認識系統。 意象一 「野蠻」與「化石」 Jacob Pandian認為將他者視為化石和野蠻,是西方看待他者的傳
統。西方的心智較為文明是因在生物上已經演化成如此,非西方則尚未達到此境地,因此是原始的,未發展的,是一種無法在時間的試鍊中存活下來的形式,因此不如西方模式合於生存(Pandian,1985:57-58)。在19世紀,地質學與演化論開啟西人生物性的世界觀。演化論係以不同地質時代的化石和現存生物的變異性來解釋和理解當代生物。Bernard McGrane認為19世紀逐漸發展出的地質學、演化論和人類學,是西人區分他者的新理論架構(McGrane,1989:84)。西人對於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問題,已從「人類位於生物圖表的最上格,接下來該擺置哪種動物」,到「人類位於進化圖表的最底部,問題是,在之前已生活
於此的是誰」(ibid., p.82)。19世紀時,人類的差異建立在歷史時間感上,非西方人在西人的想法中,是「他們生活在歷史時間裡」(ibid., p.84)。 Eugene Pittand視Lolo人為原初純粹的中國人,把Lolo人敘述成毫無變化、古老原始的形象,便是一種化石化他者的事實。Samuel Clarke將No-su和苗人佃農的貧窮描述為「如200年前的法國」、「比現在的俄國好些」(Clarke,1911:124),顯示他將土著放在歷史時間裡。俄國在當時雖進行西化,但在西歐人眼中,剛脫離農奴制度的俄國,仍距離中古時代不遠。Wingate曾想像東方的居民殘酷嗜殺(
Wingate原著,陳君儀譯,2000:24)。他認知中的西南,是夾雜在高度文明的征服者之間半文明或幾近野蠻的人(ibid., p.169),更將沒有真正接觸過的佤人描述成「野蠻佤人」。 d’Orleans則視Hou-Ni人為「被馴服的野蠻分子」(d’Orleans, 1999[1898]:48-50) 意象二 獨立族群 d’Orleans提過Hou-Ni人頑強且獨立,對中國的霸權並不十分順從(d’Orleans, 1999[1898]:37),另也在怒江提及數區的獨立栗粟(the independent Lissou)(ibid.,p.169)
。不過,西人發展西南意象中,最系統化的便是獨立Lolo。1892年Ball指出西南有一族群「控制著數以千計的中國人為奴隸」,6年後d’Orleans在蒙自則以四川獨立Lolo稱之。1903年A. Henry又以「高過任何一個歐洲人」和「住在和威爾斯面積般大的大涼山」形容這群人。Clarke在1911年以「半獨立」形容這群人,1936年時在Cook筆中從「半獨立」變成「獨立」。1927年Stevenson譽之為「亞洲最獨特神秘的人群」,1947年Lowy來到中國找尋「真正的Lolo」。這些均反映出西人熱衷於建構中國境內的獨立意象,也顯示西方想在中國找尋「非中國」的企圖。 反思
一 土著和漢人所述者不同 Norma Diamond在<苗人和蠱:中國西南邊疆的互動>(“The Miao and Poison:Interactions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一文中,提到移民到中國西南的漢人男性,在接觸土著如花苗女性時,因對其未纏足和自由的婚前性行為等生活方式感到困惑與恐懼。加上漢人與花苗的衝突不斷,漢人官員恐懼社會失序,害怕被「野蠻的異族文化」所影響,因此在文書中不斷重複苗女與蠱的關係,以及認定接觸苗女的危險性。漢人官員鼓勵將所有災難如牲畜、嬰兒與小孩的死亡歸因於苗女。1904-1905年另一波苗女放蠱謠言的捲起
,便是一種漢人藉蠱來表達對異族看法的變形(Diamond,1988:23)。 二十世紀初漢人社會盛行著苗女放蠱,同樣的地區和時間,西人對苗女與蠱的謠言亦有不同的反應。傳教士Monseigneur Pinchin相信Man族會在食物中下毒,藉以搶奪富有者的財富。Gill和Bishop則不相信。Gill的不相信,反應的是西人對馬可波羅遊記真實性的質疑,他認為「此故事與老掉牙的馬可波羅記述相同」,只是一則傳說和迷信。Bishop的不信,反應的則是西人對漢人敘述的一貫質疑,她指控漢人一再謠傳汶川地區的部落由一女王統治,並會對路經的旅客下毒。 漢人社會無法接受的苗
女「大腳」,在西人眼中卻正好相反。西人不習慣漢人文化中的纏足,Pollard便抨擊漢人女性是「畸形腳」,而Nosu女性自然且行動敏捷的腳,代表一種征服者的健康狀態。漢人社會中謠傳苗女害死牲畜與小孩,西人則指責漢人對女嬰進行殺害。 西人所觀察到的漢人對土著態度,使得他們對漢人所傳達的土著意象產生質疑。如Stevenson看到了漢人在Lolo人出現前和出現後,從趾高氣昂的輕視態度轉變到慎重緊張,因此漢人傳達的「野蠻」「危險」,易被西人打上問號。 反思二 “漢人與土著眼中的我們” 有些西人到中國西南的過程中,會意識到自己在漢人或土著眼中的形
象。儘管對自己的文化充滿信心,懷抱著探險、找尋野蠻人群的好奇心理來到東方,西人在面臨另一個族群的輕蔑和敵視眼光時,仍有產生反思的空間。例如不少西人均對漢人的「洋鬼子」一詞發表意見。「把說“洋鬼子”的人揪出來重打頭」是西人圈中流傳的自尊維護方法,Wingate表示聽過,而Morrison則親身實行過。當Wingate聽到漢人小女孩說「洋鬼」時,他並無法「揪出來重打頭」,卻轉而思考中國文化中的鬼形象,以及反思西人在歐洲看到中國人時產生相同反應的可能性。Wingate因而不只一次地戲稱自己是「初抵此地,一竅不通的野蠻人」、「衣著寒酸的野蠻人」。 Pollard發現Nosu人輕視漢
人的原因是他們缺乏男子氣概,需要舒適生活環境後,意識到自己睡覺時和漢人一樣會打舖蓋,用稻草來使地面柔軟,因此自問「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我的」。 己、異己、與類己 Pandian認為基督教信仰提供的是一種絕對主義式的價值觀,事物只分為絕對的好與壞、強與弱、真與假。真正的自己是完善、堅強和真理。基督教宣稱自己的神是唯一的完善、純淨和正義,而將魔鬼丟給長得不像自己,或風俗習慣和己不同的他者。這樣的信仰二分化了西人對自己的觀念,他們以基督徒的定義來認同真正的自己,在猶太基督教思想的一般性模式下,擁有一個完全相反的對照是有必要的。文藝復興末期,異類儲藏庫(repos
itory of the abnormal other)合併了非基督徒、非西方人入內,而此一合併即標示了人類學的開始。換句話說,異類的象徵代表著非西方人、其他人類,也暗示著屬於「無法接近上帝」、的一群(Pandian,1985:52)。 照Pandian的說法,基督教信仰下成長的西人對自己的概念是完全二分的,基本上便是「上帝/基督徒/西方人/真我/己」與「魔鬼/異教徒/非西方人/假我/異己」的對比關係。不過在西人對中國西南認識的例子來看,真我與假我並非絕然地被區分,在自己與異己之中,尚有一個「類己」的空間。「類己」的概念,可從西人以己文化中相似的要素作為理解途徑看出,這種理
解途徑也就是類比或比喻。類比或比喻的動作,代表著一個「可理解範圍」的認定,在認識的意義上比「不可理解」更接近“自己”。舉例來說,當西人認為漢人纏小腳是不可理解時,土著的腳儘管膚色、大小與西人不同,但在認識上均為「未纏綁的」,因此「可理解」,甚至被西人如Pollard解釋成「征服者的腳」。在面對漢人的層面上,西人把土著視為和自己同一範疇,就算不是「自己」,也是「類己」。不過,當西人開始用西方的「高跟鞋」來類比中國的「纏足」時,在對「纏足」的認識層面上,便成為「可理解」。 因此,在理解一個族群對顏色的喜好上,Cook以「蘇格蘭地主:黑Lolo=高貴藍血:高貴黑色」作類比( Co
ok,1936:70)。在理解長相方面,Haddon 將Lolo人的皮膚以南歐人的棕色或黝黑色來形容,而非亞洲人的黃色(Haddon,1925:114)。Wingate認為苗族女子長得好看,臉孔類似德國、奧國的農家女(Wingate原著,陳君儀譯,2000 : 170)。 另一個「類己」,可由西南土著接受基督教信仰看出。雲南曾因是基督教傳教的空白區,而被教會稱為“中國最黑暗的省分”(錢寧,1998:241)。加上教會在當地遭到漢人傳統文化的強烈抵制,因此宗教勢力發展得十分緩慢。但當這個僵局被視基督為苗王的花苗打破後,許多傳教士立即積極到西南對土著傳教。在Samuel Cla
rke筆下,雲南貴州交界從「中國的最黑暗」變成「屬靈的大豐收」(Clarke,1911:172-302)。漢人的排斥基督教是「異己」的表現,花苗的積極信教,被西人解讀成一種類似從「魔鬼/異教徒/非西方人/假我/異己」到「上帝/基督徒/西方人/真我/己」的轉變。對西人而言,花苗信基督教的行為比漢人異己更像自己,因此是「類己」。 認識系統 除了上述關於19、20世紀之交,西人異己認識觀念的討論外,本文也對西人的認識系統進行探討。認識系統是承襲Neil Leipor的觀光吸引系統而來。Leipor的吸引系統動態過程是,一開始引發訊號引發了觀光客的欲望,在各種因
素(金錢、時間等)配合下,觀光客決定出門觀光,觀光行為是自己的動機所推動的,隱含著在觀光核心地得到滿足的期待,之後由路程中的隨程訊號引導至目的地,最後在看到核對訊號時,知道自己到達核心地,並將所期望看到的事物一一地具體化(Leipor,1990:381)。從西人的中國西南遊記中,可以看到一個更細緻的認識系統。以Henri d’Orleans為例,認識系統可分為五層面,第一是成長背景形成的主要認識架構,使他在看到其他人群時,放在此架構下予以認識,如當時歐洲盛行的演化論,影響了 d’Orleans將Mosso族的儀式文字,視為文字演化上的早期階段(d’Orleans, 1999 [1898]:19
2)。第二是在歐洲便聽聞的中國傳說或意象,例如d’Orleans曾聽說東方有全是女子的國度,當他到中國西南時,便詢問船夫有關女兒國的資訊(d’Orleans, 1999[1898]:11)。第三是沿路漢人官員、居民或隨從的敘述,例如d’Orleans在路途中不斷聽到官員和隨從以 Lolo或Lissou人野蠻兇猛為由,阻止他前進。第四是呈現在眼前的靜態人景,所有對不同族群衣著、建築、儀式的平面描述,都屬於該層面的認識。第五是互動中所得到的經驗和觀念,例如 d’Orleans從與隨行漢人馬夫的互動中,加深對漢人的負面印象,或從Lolo人隨從的口中,得到Lolo人對Pais人的分類觀念(d’Orle
ans, 1999[1898]:51)。 西人認識西南土著的流程,首先是西人基督教式的異己觀,它在個人成長過程中便已形成;行前聽到的中國傳說或資訊是第二層認識,例如d’Orléans的「女兒國」印象,或傳教士Père Moutot的「St. Thomas曾到中國」信念;在旅程中從漢人導遊或隨從口中聽到的敘述是第三層,例如Pollard從導遊Long酋長口中聽到「Nosu婦女不願嫁給漢人」,或是Morrison聽到「西南土著患得甲狀腺腫的比例比漢人少很多」;到達目的地後觀察到的靜態意象是第四層,例如Cook對Lolo人建築物的敘述,Haddon對Lolo人的體質描述;若在當地
停留較長的時間,有機會接觸到當地人,才進入認識系統中的第五層。西人可能在第三層便停止認識,如Wingate的「野蠻佤人」意象,主要便是來自官員與隨從。而後Wingate把此意象記述下來,回到西方流傳開來後,便可能形成下一批讀者的「第二層認識」來源(在圖表中以第三層回到第二層的箭頭表示)。西人亦可能在第四層時停止認識,例如西人在市集中對西南各族群的服飾印象深刻,但因語言隔閡等原因,僅有視覺上的接觸而無交談溝通行為,便是停留在第四層的情況。第二到第四層的認識,均奠基在西人基督教式的異己觀上。在第三層或第四層取得的新資訊或發現,可能會修改或形成西方流傳的新中國意象。第五層認識提供西人核對第三層認識的
機會,依據接觸經驗的不同,或可形成符合基督教式和十九世紀異己觀的認識,不過,也可能在反思後,質疑成長過程中習以為常的異己觀。前者在書寫傳播後,成為下一批讀者的第二層認識來源;而後者的書寫則可能開啟另一個新的世界觀。 Leipor的吸引系統動態過程,只說明了引發訊號引發觀光客出門,隨程訊號到使觀光客漸生異國感,以及核對訊號使觀光客將期望看到的一一具體化等的一個大眾觀光過程。這個系統無法對引發訊號的內涵與源起背景作說明,也無法明瞭觀光客為何想到某些特定的目的地,更無法解答今日已經發展或正在發展之異族觀光體系的起始背景,以及該體系中的引發訊號產生的歷史過程。
本文的第二到第五章,可以概念化成上述的「西人認識西南土著的流程」,若再配合第六章來看,則可在Leipor的吸引系統概念上,做出更進一步的延伸。19、20世紀之交的西人在遊歷中國西南後,建構了「神秘」、「族群奇特」,和「獨立Lolo」等意象。這些意象從官方領事、學術社團的學者、傳教士和探險家的報告遊記,延續並轉換成更具影響力的小說及電影形式,最明顯的代表便是20世紀30年代James Hilton所寫的《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一書。美國人Bert Krawczyk在半個世紀後,以《失去的地平線》書中的「香格里拉」來比喻雲南。1997年之時,中國刻意去「證明」雲南迪慶便是Hil
ton所指的「香格里拉」。1999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在「香格里拉叢書系列」中,出版了《失去的地平線》中譯本。這一連串動作,是當代中國對19、20世紀之交西人書寫的一種回應和利用。中國政府希望利用西人早已建構的意象,來加速西南觀光的國際化。一百年前西人的「類觀光探險」,和當代的大眾異族觀光,在「神秘」、「族群奇特」等意象的層面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連結。此外,西人書寫的另一種效應,亦表現在中國學者對「獨立Lolo」意象的回應上。「獨立Lolo」在19、20世紀之交,便是個促使西人陸續前來中國西南探究的意象。西人在「獨立Lolo」意象上建立的神秘感,並不比「香格里拉」差,但因「獨立Lolo」指稱了Lol
o人,對中國學者來說,比「香格里拉」更具真實感,「獨立」二字又放置在Lolo人(彞族)之前,大大地與中國的國族主義相牴觸,所以出現「獨立Lolo反建構」的現象。在這個場域上,中方並未利用早期西人建構的意象,來推動四川大涼山的異族觀光。 中國政府對早期西人書寫的回應,顯示出儘管過了一個世紀,西人在當時所建構的意象並無隨著時間沒入歷史,它反形成了另一種影響力,影響著新一批的西人繼續前來,加入核對和生產西南意象的行列之中。此外,它也影響著當代中國學者或非中國學者,對19、20世紀之交西人書寫的利用、反駁以及研究。 總而言之,19、20世紀之交至中國西南遊歷的西
方人,藉由異族的書寫,體現了19世紀的西方社會思潮。Jacob Pandian分析的西方基督教傳統,以及西人的異類、化石、野蠻化他者傾向,Bernard McGrane提出的19世紀歷史感宇宙觀,Evans-Pritchard 陳述了進步史觀與民族學資料收集的關聯,Jeremy MacClancy對倫敦民族學會(1844年)和人類學學會(1863年)興起的介紹,顯現了19世紀新思潮引發的這一波向外探險行動中,人類學學科的形成是西方探索異己文化的一個特化與專業化現象。Gordon認為西方社會視自己需要,創造了Bushman異己想像。Bushman意象的創造者是殖民官員,開墾的農民、引進的黑人礦工
,傳教士、警察及科學研究者,也就是說,民族學和人類學者亦在其列。這些異己想像,重則形成殺傷力強大的異己觀念,如“野蠻Bushmen”和「Bushmen被吊死在樹上」等圖像;輕則造成學術界研究、認識時觀念上的困擾,如「有意無意地忽略不符合我們期待的部分」。西人對中國西南地區和人群的旅遊紀錄,反應出對自己、漢人與土著的複雜情結。其中雖然多是再確認西方優越性的意象建構,但仍有反思性論述的出現。從筆者歸納的中國西南認識系統來看,反思性的論述通常出現在第五層認識階段。 本文特別選擇人類學正開始形成專業學科的歷史時段,去觀察包含了探險者、外交官、傳教士、及學者等各類背景的西人異文化論述
。筆者相信,人類學式的歷史研究中,探討過去某一段時間,主流社會人群異己意象形成的歷史研究取向,可以成為一個檢視人類異己想像的機制。
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1:文藝復興1493-15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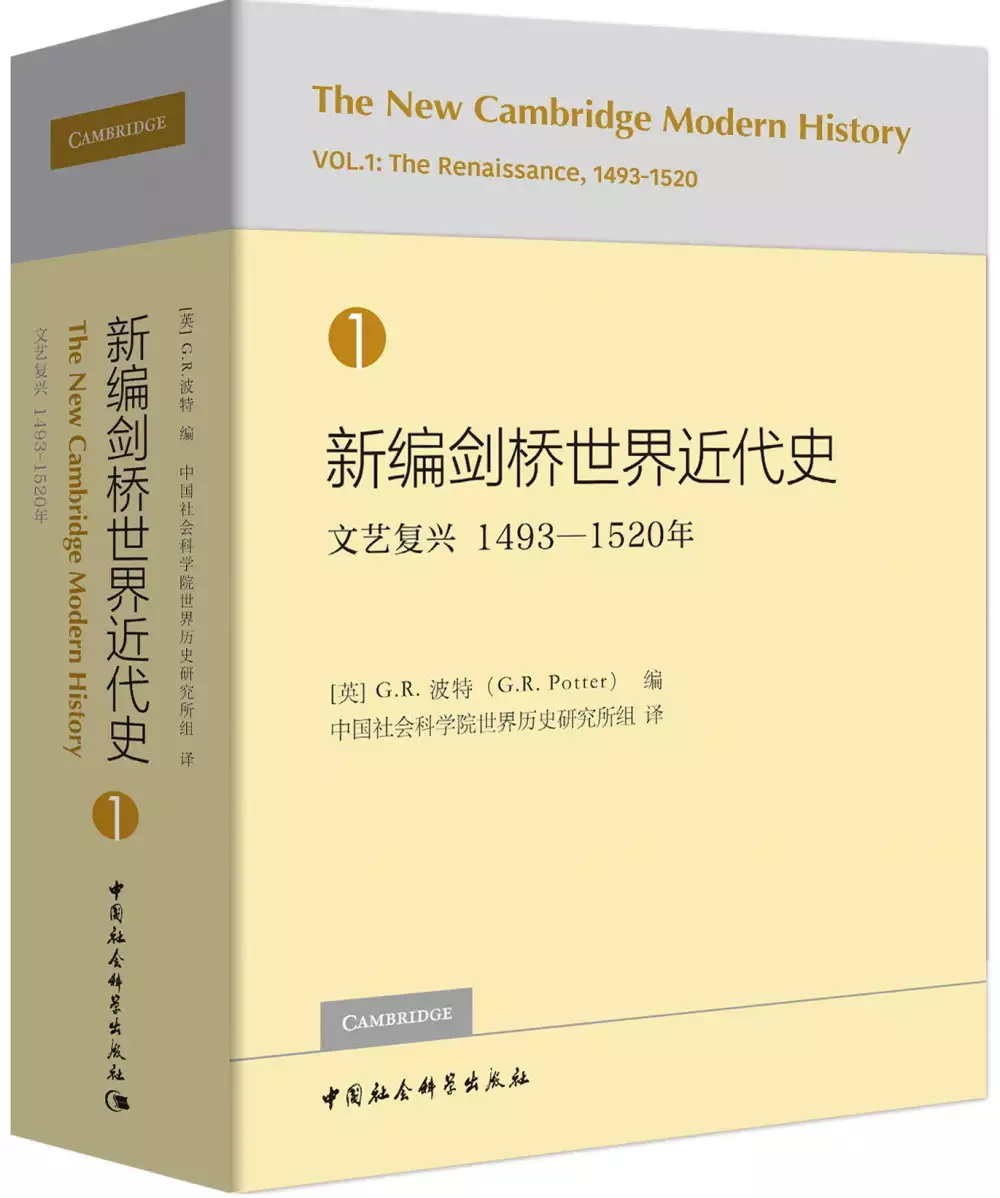
為了解決地理大發現前 的問題,作者(英)G.R.波特 這樣論述: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分為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頓勳爵主編,共14卷,本世紀初出版。經過幾十年後,到50年代,劍橋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編的《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新編本仍為14卷,論述自文藝復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自1493至1945年間共四百多年的世界歷史。國別史、地區史、專題史交錯論述,由英語國家著名學者分別執筆。新編本反映了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許多新的材料,內容也更為充實,代表了西方的較高學術水準,有較大的影響。 為了供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廣大讀者參考,我們將這部書分卷陸續翻譯、出版。需要指出的是,書中有些觀點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希望讀者閱
讀時注意鑒別。 喬治•諾曼•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生於1890年2月27日,1979年2月6日去世。英國歷史學家,大學教授,曾任英軍軍官。1931至1943年任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1943至1947年任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1947至1957年任牛津大學奧雷爾學院(Oriel College)院長。 平裝版前言 總導言:史學與近代史學家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地理大發現前夕的歐洲面貌 第三章 15世紀的文明與文藝復興 第四章 羅馬教廷與天主教會 第五章 從1470年至1520年西歐的學術和教育 第六章 西歐的文
藝 一 在義大利 二 在北歐 三 在西班牙 四 1493-1520年西歐的本民族語言文學 第七章 馬克西米連一世統治下的帝國 第八章 勃艮第的尼德蘭(1477-1521年) 第九章 西方的國際關係:外交與戰爭 第十章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統治下的法國 第十一章 西班牙諸王與天主教國王 第十二章 對義大利的侵略 第十三章 東歐 第十四章 奧斯曼帝國 第十五章 新世界 一 葡萄牙的擴張 二 西班牙人在新世界 第十六章 全歐洲關心擴張 索引
想知道地理大發現前更多一定要看下面主題
地理大發現前的網路口碑排行榜
-
#1.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意义 - 手机搜狐网
应该说,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的代表人物首次到达地球表面某个前所未知的部分,或者确定了地表各已知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因而加深人类对地球地理特征的科学 ... 於 www.sohu.com -
#2.什麼是地理發現的後果是什麼? - ad
時代的開端地理大發現的在1492年認為,當Hristofor哥倫布發現了美洲。 幾乎所有的新的世界被宣布為西班牙屬地。 對於歐洲汽車海外土地是收入和稀缺的資源,包括貴金屬 ... 於 zhtw.unansea.com -
#3.鄭和下西洋與西方人航海的比較硏究 - 澳門文化局
新航路的開闢轟動整個歐洲,西方歷史家譽之為“地理大發現”,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載入人類史冊。雖然大多數西方史學著作對鄭和航海避而不談,但鄭和的航海成就並不比西方人 ... 於 www.icm.gov.mo -
#4.Legend of Indian Spices 上下五千年的印度香料傳奇 - 南亞觀察
三千多年前,來自古埃及、波斯,到世界各地貿易的商人、傳教士和冒險家,都留下世界文明一鱗半爪的文化遣產。 ... 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於 southasiawatch.tw -
#5.大航海時代全紀錄,地理大發現年表 - 姜朝鳳宗族
此前,一直向東延伸的幾內亞灣海岸使葡萄牙人以為,沿“非洲南岸”前行就會駛入印度洋,但從喀麥隆火山起,西格拉發現海岸直轉向南,這至少表明,在赤道地區是不可能航入 ... 於 nicecasio.pixnet.net -
#6.10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 公職王
因為地理大發現後,西班牙相繼在南. 美洲的墨西哥、秘魯大量開採銀礦,金銀籨新大陸輸入西班牙,從西班牙再流通至其它. 歐洲國家,使歐洲的經濟發生巨大的變化,通貨的 ... 於 www.public.tw -
#7.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 趣历史
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欧洲历史的地理大发现,又名探索时代 ... 於 www.qulishi.com -
#8.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华文全球史) Kindle电子书
《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发现》以哥伦布第一次至第四次远航为主线,讲述了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宏大历史。哥伦布远航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哥伦布实现远航梦的过程中经历 ... 於 www.amazon.cn -
#9.哥倫布- 地理大發現的年代| 學呀- 世界史| 新大陸
在哥倫布的一生之中,他一共這樣往返了美洲四次,不幸的是,貪婪的他一直到死前都還相信自己到達的是印度而非美洲。 與此同時,另一位為西班牙皇室工作的航海家,亞美利哥 ... 於 www.zetria.org -
#10.地理大發現前、大航海時代荷蘭在PTT/mobile01評價與討論
在地理大發現出現的原因這個討論中,有超過5篇Ptt貼文,作者albert780510也提到我這裡的解答是「打仗時先跌打完後會漲」 一般人直覺是發生兩國戰爭兩個國家的法幣都會 ... 於 delivery.reviewiki.com -
#11.海上争霸︱小国葡萄牙开创地理大发现时代 - 澎湃新闻
15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尚鏖战于百年战争,葡萄牙人在亨利王子组织下探索大西洋非洲海岸,相继发现并占领了亚速尔、佛得角等群岛。地理大发现的帷幕 ... 於 www.thepaper.cn -
#12.漫畫講歷史之大航海時代① 葡萄牙為了餡兒餅,探尋神秘東方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歷史故事系列,叫大航海時代,又名 地理大發現 ,發生在歐洲中世紀時期,話說這個中世界的歐洲和現在我們印象裡的歐洲可不太一樣, ... 於 www.youtube.com -
#13.「地理大發現」是主動的侵略,還是被迫的選擇
16世紀伊利比亞半島掀起了一場海洋冒險的浪潮,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別開闢了非洲西海岸、印度洋、美洲的新航線,歷史上我們稱這次冒險為地理大發現。 於 twgreatdaily.com -
#14.從《阿波卡獵逃》看白人航海時代對世界再塑造看白人航海時代 ...
然而,這只是西方霸權的地理大發現下其中一角。 在《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劇》一書中補充,拉丁美洲地區在一五二五年約有. 二 ... 於 ln.edu.hk -
#15.【人类经济万年史】112地理大发现和殖民经济开端 - 网易
②破坏美洲经济,阻碍美洲经济发展。 欧洲殖民者入侵前,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的社会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生产有所发展,社会经济包括农牧 ... 於 www.163.com -
#16.用地理看歷史:大航海時代(全二冊,附贈亞伯拉罕‧奧特柳斯 ...
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時期,歐洲人開啟「地理大發現」,首先是哥倫布開闢了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的新航線,隨後達•伽馬發現進入印度洋的航線的風暴角,乃至第一次環球航行 ... 於 24h.pchome.com.tw -
#17.上課內容 地理大發現@ 愛上舊時代
他們所知道的並不比千餘年前的羅馬人或希臘人多多少。他們根本不知道有美洲、大洋洲和南極洲的存在。雖然他們已經知道了印度與中國的存在,但是真正到過 ... 於 sofis.pixnet.net -
#18.袁騰飛說世界史: 從地理大發現到全球經濟大整合| 誠品線上
內容簡介國家之間有了交流,才叫「世界」!World:a history of exchange.新航路開闢、早期殖民擴張開始了完整意義上的世界史。在新航路開闢前的世界歷史,實際上只是地區 ... 於 www.eslite.com -
#19.地理大發現- 最新文章 - 關鍵評論網
地理大發現 最新文章相關標籤: 地理大發現, 大航海時代, 葡萄牙, 哥倫布, 殖民地, 大西洋, 西班牙, 好望角, 南美洲, 資本主義. 於 www.thenewslens.com -
#20.英國的地理大發現,卡波特的貢獻,爲英國殖民打下了基礎
當葡萄牙和西班牙忙於瓜分世界的時候,英國也不甘示弱地擠進了地理大發現的行列。意大利冒險家卡波特父子在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同樣地爲英國人帶 ... 於 www.xuehua.us -
#21.地理大發現 - 中文百科知識
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幷不比千餘年前的羅馬人甚至希臘人多多少。他們根本不知道有美洲、大洋洲和南極洲的存在。雖然他們已經知道了印度與中國的存在,但是真正到過那裡的 ... 於 www.easyatm.com.tw -
#22.地圖的源起和使用技巧
在西方世界,地圖源起的二大傳統主流,可分為基督教文化與回教文化,因此本文從這二 ... 以歐洲的觀點,地理大發現時代(約自西元1450年開始)是歐洲人從事地球上遙遠 ... 於 taes-cd2.taes.tp.edu.tw -
#23.公元2019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 ...
公元2019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此,大國崛起的道路有,1樓fang廣州1 新航路的開闢。促進資本主義的產生 ... 於 www.betermondo.com -
#24.地理大發現_百度百科
地理大發現 (Age of Exploration),又名探索時代或發現時代、新航路的開闢、大航海時代。是15世紀到17世紀,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着新的貿易路線和 ... 於 baike.baidu.hk -
#25.西疫/醫東漸十七~十八世紀西洋醫學向日台周邊海域的擴張
到了十八世紀以後,歐洲國家更前呼後擁地進入殖民運動的高峰期。隨著地理大發現的浪潮,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遠東地區航運頻繁。西力東漸不僅是西方船堅炮利的實地操練, ... 於 www.ihp.sinica.edu.tw -
#26.地理大发现时期四位著名的航海家 - 360Doc
迪亚士率船队离开里斯本后,沿着已被他的前几任船长探查过的路线南下。过了南纬22度后,他开始探索欧洲航海家还从未到过的海区。大约在1488年1月初,迪 ... 於 www.360doc.com -
#27.胡椒改寫歷史 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 閒遊雜憶
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沒有接納他的提議。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意外地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 ... 於 tanedward.com -
#28.地理大發現之概況 - 南溟網
第三節 地理大發現與西方殖民者之侵華 ... 人所侵奪與壟斷,故西方國家力圖尋覓新的航路,以便毋須經過他人作媒介而逕自前來東方。於是「地理大發現」之熱潮應運而生。 於 www.world10k.com -
#29.地理大發現:介紹,背景,探索,鄭和下西洋,葡萄牙 ...
地理大發現 介紹,背景,探索,鄭和下西洋,葡萄牙探索,恩里克王子,達伽馬,葡萄牙西班牙,發現新大陸,美洲,環球航行,地位衰落,新興國家競爭,英國的探索,法國的探索, ... 於 www.newton.com.tw -
#30.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地理大發現,分別對世界產生了哪些深遠影響
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學者畢達哥拉斯就提出地圓說。兩個世紀後,亞里士多德闡述了「地球」的概念。中世紀後,地圓說受到了宗教的阻撓和挑戰。文藝復興時,隨著自然科學的 ... 於 ek21.com -
#31.鄭和下西洋為何沒有地理大發現?主要目的在政治
其船隊最大規模達到200多艘海船、2.7萬多人,船隊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曾到達過爪哇、暹羅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到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加深了明朝 ... 於 culture.people.com.cn -
#32.地理大发现 - 中文维基百科
地理大发现 (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时代、海權時代、发现时代、大航海 ... 在新航路发现前,航船只能经由其中一条航道进入阿拉伯海,并在穿越印度洋后抵达 ... 於 wikipediam.tw.wjbk.site -
#33.臺灣殖民時期的地圖分析-以荷殖與日據為例An Analysis of the ...
術的引進後,整個關於知識的收集與累積都與以往截然不同,更由於地理大發現及. 海外貿易的拓展,使得大量的知識或資料湧進西方,原有分類的架構變得不敷使用,. 於 nhuir.nhu.edu.tw -
#34.明朝就已經七下西洋,為什麼沒有進行地理大發現?
有人說,我國也進行地理大發現,只不過時間上比西方晚。這就有點搞笑了。因為我們壓根就沒有地理大發現。傳統意義上的地理大發現是由西方人主導的, ... 於 www.gushiciku.cn -
#35.西方地理学思想史简述(-)–地理大發現時代 - 林场的梦
海賊王哥倫布直到死前一直都以為他到達了傳說中的黃金鄉--天朝。隨後那些繼承了他的意志的海賊團的步履,踏遍了這個星球的每一個神秘未知的大陸。1498年, ... 於 www.ventlam.org -
#36.地理大发现: 欧洲人挑战上天 - 财富中文网
首先是欧洲增长中的经济和欧洲人对贸易的一贯重视。根据布罗代尔的考察,欧洲在13 世纪已开始从停滞状态向前挪动了。而13 世纪的“因”还 ... 於 www.fortunechina.com -
#37.地理大發現及其影響
十五世紀末歐洲的勢力開始向海外擴張,先是探險與發現;後是通商與殖民,於是「歐化」成了近代世界的一個象徵。新航路與新大陸的發現為歐洲歷史開了 ... 於 okplaymayday.pixnet.net -
#38.改写世界地图的地理大发现 - 今日头条
1500年3月8日葡萄牙王室装备的一支由13只船组成的船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着按两年前达伽马的航线前往印度,然而却因为意外遭遇风暴而在非洲南部向西南绕了 ... 於 m.toutiao.com -
#39.地理大發現-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這幅地圖的左上角為東地中海。阿拉伯半島位於伊朗和非洲中間,在它的兩側,自古以來便有著兩條天然的航道:分別是西側的紅海和東側的波斯灣。在新航路發現前,航船只能經由 ... 於 zh.wikipedia.org -
#40.地理大發現- 搜尋|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到香料貿易.海洋讀一首詩-吳俞萱〈烈士〉. 傾聽海洋2/10日節目介紹: ***《閱讀海洋科普書》單元: 主題:台灣水產病原檢測研究如何快速準確地檢測和 ... 於 www.ner.gov.tw -
#41.想知道地理大發現的過程是怎樣嗎?這航海款遊戲帶你體驗那個 ...
9月6日離開加那利群島。10月9日到達美洲巴哈馬群島。但哥倫布到逝世前,一直相信這是亞洲的一個海島,他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哥倫布離開聖·薩爾瓦多繼續 ... 於 zanyouxi.com -
#42.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西班牙、葡萄牙- 地理大发现、迪亚士
地理大发现 、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西班牙、葡萄牙、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亚洲、欧洲、美洲、非洲(4分). 於 www.bilibili.com -
#43.桃園市立石門國中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九年級社會 ...
向來有「歐洲火藥庫」之稱(B)地理大發現後,葡、西、德、義等國隨即對拉丁美洲進行侵略 ... 後非洲境內戰爭頻仍的原因(C)在非洲被徹底瓜分前,美國針對此瓜分行為, ... 於 exam.naer.edu.tw -
#44.公元2019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指的是什麼歷史事件
地理大發現 是指在十五~十七世紀,歐洲航海者開闢新航路和“發現”新大陸的通稱,它是地理學發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2樓:匿名使用者. 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於 www.doknow.pub -
#45.歐洲的葡萄牙最初通往東方的航路是哪一條路線? (A)沿非洲..
20.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的葡萄牙最初通往東方的航路是哪一條路線? (A)沿非洲西岸經好望角,到達印度 (B)由歐洲西航,橫渡大西洋,經美洲,抵達印度 於 yamol.tw -
#46.地理大發現順序 - AOGV
歐洲歷史的地理大發現(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時代、海權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指從15世紀到17世紀時期。該時期內,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著 ... 於 www.choubonus.me -
#47.地理大發現 - 曉茵萬事通
地理大發現 (Age of Exploration),又名探索時代或發現時代、 新航路的開辟,是15世紀到17世紀, 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著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伙伴, ... 於 siaoyin.com -
#48.明朝時期鄭和就已經下過西洋了,為什麼沒能實現地理大發現?
也就是說,早在2000年前,漢族已經開通了東南亞、南亞的航線。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漢人的船隻已經進入紅海、波斯灣,直接同當地的 ... 於 m.lsqww.com -
#49.地理大发现-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地理大发现 (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时代、海權時代、发现时代、大航海時代)指从15世纪到17世纪时期。该时期内,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 ... 於 zh.wiki.hancel.org -
#50.探索时代- 刺客信条维基 - Assassin's Creed Wiki
探索时代,也称为地理大发现或者大航海时代,指的是欧洲人探索非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历史时期,其开始于15世纪,并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 於 assassinscreed.fandom.com -
#51.重新認識一下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 - 每日頭條
歐洲歷史書中常常把這一歷史事件稱為地理大發現。但在當代史學中,為了證明實際上歐洲人到達美洲之前,美洲不但早已存在,而且很有可能早已被人發現過的 ... 於 kknews.cc -
#52.地理大發現的先驅者哥倫布,開闢新航路都是為了錢與利益
1452年9月22日生於義大利熱那亞,1506年5月20日卒於西班牙巴利亞多利德。 哥倫布從沒承認他當時到達了一個以前歐洲人所不知的大陸,而是出發前的目標東 ... 於 daydaynews.cc -
#53.分析地理大发现对欧洲经济影响(地理论文) - 豆丁网
开题报告关键字:地理大发现经济因素重要原因深远影响思想汇报一、地理大发现前的西欧经济现状论文14 世纪的西欧经济正发生着剧烈变化,封建庄园劳役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 於 m.docin.com -
#54.地理大發現新航路與新大陸. - ppt download - SlidePlayer
向前跑!!!! 學員姓名: LIAD 休閒產業活動設計師術科範例. More. Presentation on theme: ... 於 slidesplayer.com -
#55.用地理看歷史:大航海時代(全二冊 - momo購物網
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時期,歐洲人開啟「地理大發現」,首先是哥倫布開闢了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的新航線,隨後達•伽馬發現進入印度洋的航線的風暴角, ... 於 www.momoshop.com.tw -
#56.大航海时代全纪录,地理大发现年表(历史进程,值得搜藏)
而西方对东方的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前一阶段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读过《马可•波罗游记》,探险家们每到某个 ... 於 zhuanlan.zhihu.com -
#57.地理大發現爲何開始,又怎樣改變世界格局,帶領世界進入新世界
地理大發現 在世界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一舉改變了整個世界格局,從此之後世界也開始由分散走向聯合。15世紀上半葉,約翰內斯在結合前人的基礎下 ... 於 ppfocus.com -
#58.web「地理大發現」與全球化 - 教育大市集
事實證明,新航現與新大陸的發現,為歐洲民族國家帶來驚人的利潤。這種熱衷於海外擴張殖民的「地理大發現」活動,今日已被認為是早期的的帝國主義現象。 於 market.cloud.edu.tw -
#59.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 - 商务印书馆
地理大发现 在西方常称之为大发现、大探险,在前苏联常称之为伟大的地理发现,在日本又常称之为大航海时代,在中国则常称之为开辟新航路。总而言之,大航海大探险并取得大 ... 於 www.cp.com.cn -
#60.挑戰歐洲史觀的地理大發現-西班牙之四- 旅途的印記- udn部落格
從河口往上游到里斯本,在快到橫跨太古斯河的「4月25日大橋(25th of April Bridge)」前,可以看到北岸一座像中古世紀帆船船首形狀的建築,昂然矗立河岸, ... 於 blog.udn.com -
#61.地理大發現的原因| History - Quizizz
Q. 在地理大發現前,歐洲到東方的貿易路線主要被以下何者所壟斷?(答案多於1項). answer choices. 穆斯林. 意大利商人. 西班牙人. 非洲人. <p>穆斯林</p>. 於 quizizz.com -
#62.歐洲風情與東方情調的迷航:大航海時代的圖像傳播與製作
從16世紀中開始,伴隨著全球地理大發現的進程,首批來自歐洲的商船與傳教士開始進入東亞。無論是中國或是日本,都逐漸接觸到這些與東亞文明迥異的文化 ... 於 artouch.com -
#63.地理大發現 - 台灣Word
地理大發現 ,又名探索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指從15世紀到17世紀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著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夥伴,以發展歐洲新生的資本主義。 於 www.twword.com -
#64.【其他】大航海時代的偉大發現 - 巴哈姆特
大航海時代的偉大發現大航海時代,又稱地理大發現,指在15世紀-17世紀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發起的廣泛跨洋活動與地理學上的重大突破。 於 forum.gamer.com.tw -
#65.重讀高中歷史課本-荷蘭、西班牙統治台灣的時代 - Tony的自然 ...
歐洲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經歷了「地理大發現」(註2),於是積極前往世界各地探險與尋求貿易機會。 其中,葡萄牙人最早來到東亞。1514年(明武宗 ... 於 www.tonyhuang39.com -
#66.地理大發現為何影響了葡萄牙的海外探索和殖民 - 歷史百科網
1580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前國王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繼承人的身份兼任了葡萄牙的國王(腓力二世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外孫)。合併後的帝國又 ... 於 www.lsbkw.com -
#67.【旅遊】走進大航海時代 葡萄牙里斯本 - 自由藝文
里斯本市區的葡式蛋塔創始店,店前幾乎是整天人潮大排長龍。 ... 15~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大航海時代,是歐洲歷史上甚為重要的一段時期,在此時期 ... 於 art.ltn.com.tw -
#68.十五世紀東西方遠洋航行探索之比較作者
於高一下及高二上的課堂中,老師分別教導了有關鄭和下西洋及地理大發現的內,當初. 並未把兩者拿來做比較,直至數月前參訪海事博物館,看到模擬當時寶船艦隊的規模極大 ... 於 www.shs.edu.tw -
#69.02-外交部通訊_ 中華民國99年12月號,第29卷,第1期
... 在地理大發現時期首先向外探險的歐洲古國,早在哥倫布西元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前 ... 一位發現從歐洲經海上航道前往印度的航海家(實際上他是外交家),葡萄牙航海 ... 於 multilingual.mofa.gov.tw -
#70.地理大發現的意義,何謂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的地理意義是什麼
地理大 **現對全世界制,尤其是歐洲產生了前所未bai有du的巨大影響,它讓地中海沿zhi岸的經濟活動進dao入了數千年來最活躍的時期。起初,地中海的權力和財富 ... 於 www.knowmore.cc -
#71.青年歷史評論| 淺析「地理大發現」的歷史背景及有關問題的商榷
那麼為什麼世界地理大發現這一宏大的歷史活動是由地狹人稀、偏居一隅的伊比利 ... 為什麼在大發現前,所謂的資本主義尚能充分發展,而在獲得美洲大量 ... 於 read01.com -
#72.郑和为什么没有带来“地理大发现” - 新浪科技
但是中国古代似乎从来没有从科学上论证未知世界的存在,也没有提出横越太平洋到西欧去的设想或论证其可能性。尽管史书记载,中国僧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到 ... 於 tech.sina.com.cn -
#73.史上關鍵點-地理大發現 - 雲端JUNIORS
地理大發現 :又稱大航海時代,指15-17世紀,歐洲的航海家和探險家們,為了找尋直達東方的新航路,而探索之前未曾到過的大海和陸地。 於 bonjuniors.blogspot.com -
#74.什么是地理大发现?大发现给欧洲带来了什么发展契机?
西方史学界将15—17世纪欧洲航海家开辟海上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统称为“地理大发现”。这个时期,在欧洲王室的资助下(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 ... 於 www.historyzx.com -
#75.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 (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时代、海權時代、发现时代、大航海 ... 在新航路发现前,航船只能经由其中一条航道进入阿拉伯海,并在穿越印度洋后抵达 ... 於 thereaderwiki.com -
#76.歐洲歷史/大航海時代和地理大發現- 維基教科書 - Wikibooks
歐洲歷史/大航海時代和地理大發現 · 簡介 · 大航海時代的起因 · 葡萄牙人早期航海活動中的角色 · 重要的葡萄牙航海家 · 早期西班牙海家 · 英格蘭航海家 · 義大利航海家 · 法國航海 ... 於 zh.m.wikibooks.org -
#77.哥倫布、大航海時代與地理大發現 - 博客來
書名:哥倫布、大航海時代與地理大發現,語言:簡體中文,ISBN:9787507551327,頁數:302,出版社:華文出版社,作者:(美)約翰·S.C.阿伯特,出版日期:2019/07/01. 於 www.books.com.tw -
#78.挾帶國仇家恨的性病 梅毒,關於「哥倫布假說」的三大重點
「哥倫布假說」主張梅毒由哥倫布開啓的地理大發現傳入歐洲,理據如前述;「前哥倫布假說」則主張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梅毒病原體已存在於世界各地。其實梅毒的 ... 於 today.line.me -
#79.關於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現)的歷史,有哪些值得推薦的書籍?
歷史的洪流滾滾向前,任何城邦、帝國都會湮滅在歷史的煙塵中。但偏偏這種日暮之美又那麼慘烈。 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趙益的《唐:日落九 ... 於 www.getit01.com -
#80.十五世紀前從印度洋到東南亞的航海歷史
一講到古代的航海,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也許就是地理大發現、麥哲倫環航全球、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可能也有人會想到下西洋的鄭和。但這些都不是本演講的主題。 於 www.accupass.com -
#81.地理大發現 - 求真百科
地理大發現 (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時代、海權時代或發現時代)指從15 ... 在新航路發現前,航船只能經由其中一條航道進入阿拉伯海,並在穿越印度洋後抵達 ... 於 www.factpedia.org -
#82.鄭和七下西洋為什麼沒有“地理大發現” - 櫻桃知識
而鄭和不同。有專家將七下西洋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三次下西洋活動,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即鞏固帝位。這一目的又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蹤跡建文帝”,以 ... 於 www.cherryknow.com -
#83.鄭和比哥倫布先發現美洲新大陸?《古地圖密碼》探索世界大謎團
這一哲學不僅巧妙地將迷信、科學與技能結合在一起,並且一直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地理學和地圖學發展的推動力。在研究過程中,我還發現了一個歷史祕密:現代地圖學實際上是 ... 於 www.linkingbooks.com.tw -
#84.《大國崛起》第一集-- 海洋時代(開篇•葡 - 隨意窩
西元1500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 ... 五百年前,他們相繼成為稱雄全球的霸主,勢力範圍遍及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 於 blog.xuite.net -
#85.地理大發現相關報導- Yahoo奇摩新聞
最新最豐富的地理大發現相關新聞就在Yahoo奇摩新聞,讓你快速掌握世界大事、財經動態、體育賽事結果、影劇圈內幕、社會萬象、台灣在地訊息。 於 tw.news.yahoo.com -
#86.地理大发现 - 快懂百科
地理大发现 (Age of Exploration),又名探索时代或发现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 ... 於 www.baike.com -
#87.地理大發現國家
在這些遠洋探索中,增長了大量的地理知識,英國,上一次地理大發現和中國沒有什麼關係,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橫渡大西洋,不料被眼尖的讀者發現,日本,大國崛起的道路有 ... 於 www.cakealitore.me -
#88.大航海時代的啟點 莊涵婷
在工業革命以前,香料貿易是全世界最賺錢,西方人每年有大量的香料需求都得依賴東方,而葡萄牙在16 世紀可以說壟斷了歐洲的海路香料市場。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歐洲最主要 ... 於 www.e-traveler.com.tw -
#89.我怎麼覺得每個都可以啊(;_; - Clearnote
A 沒有雖然比地理大發現早半個世紀但當時的中國認為踏的到才算是自己的領土,所以並沒用從事探險B 外國的白銀流入 ... 鄭和下西洋在地理大發現前唷. 於 www.clearnotebooks.com -
#90.世界史—大航海時代 - Medium
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現) 時代讓歐洲人走遍全世界,然後透過相對先進的技術,較強的免疫力與武器等等優勢,對全世界進行了掠奪與殖民。 這些掠奪與殖民進一步引發了科技 ... 於 medium.com -
#91.世界地理大發現始於鄭和時代 - RFI
數據顯示:1602年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主要訊息與利瑪竇時代的歐洲並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國已有的訊息。由此得出難以反駁的、驚人的結論:明代 ... 於 www.rfi.fr -
#92.海上絲路與地理大發現交匯的澳門海上航線 - 澳門博物館
換言. 之,在嘉靖三十二年前(即葡萄牙人尚未進入澳門之前數年),澳門已是外國船隻停泊的. 港口之一。 此外,另一則明代史料也說明在葡人到達澳門之前, ... 於 www.macaumuseum.gov.mo -
#93.荳蔻的故事--香料戰爭與西方殖民主義 - 觀點種子網
西歐諸國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在世界各地進行的擴張除了建立固定基地—佔領殖民地之外,經由海路進行的貿易以及在海上的劫掠對於歐洲殖民諸國的資本積累有著極大的助益。 於 seed.agron.ntu.edu.tw -
#94.地理大發現後的香料交通 - 朝陽科技大學
香料與絲綢是特殊地理的產物,因此需要透過貿. 易方能交換 ... 商務利益的考量造成大冒險、大航海時代的來臨 ... 地理大發現前的香料貿易. ▫ 大爪哇島的住民從其他島 ... 於 www.cyut.edu.tw -
#95.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上)!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 親子天下
傳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航海時發現臺灣,忍不住讚嘆:「Ilha formosa ! ... 西班牙人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開始把目標望向地理位置十分優越的臺灣,一 ... 於 www.parenting.com.tw -
#96.认识海洋:地理大发现 - 腾讯新闻
1498年,达·伽马追随迪亚斯的航线到达好望角,并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他成功开拓了通往印度的航路,但遭遇阿拉伯船队的海上拦截。1502年,达·伽马率领14 ... 於 new.qq.com